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冲刷出无数兴衰成败的印记。
司马光穷尽心力编纂的《资治通鉴》,不仅是一部帝王教科书,更是一本人性洞察的百科全书。
梁启超曾言:“读《资治通鉴》者,如饮醇醪,不觉自醉,以其叙兴亡,明因果,示劝戒,最足发人深省也。”
在这部巨著的字里行间,反复印证着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洞悉人性,特别是其趋利避害的复杂本质,往往是决定成败荣辱的锁钥。
古往今来,能成大事者,莫不精于此道。
他们或能预判人心向背,或能驾驭利害纠葛,或能在人性的迷宫中找到那条通向光明的路径。
翻开这部煌煌巨著,让我们跟随古人的足迹,结合近世的回响,探寻那隐藏在成败背后的幽微人性。

《资治通鉴》开篇不久,战国初年的风云便扑面而来。
魏文侯欲启用平民段干木,其弟魏成力荐,言段干木“守道不仕”的高洁。
文侯亲至其闾,段干木逾墙而避,文侯反而愈加敬重,每过其门必轼。
然而,当文侯欲伐中山,需要得力干将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善用兵、能征伐的李克(又名李悝),而非仅具道德声望的段干木。
司马光于此评道:“文侯能尊贤者而显用之,亦能知所急先务也。”
他精准地判断出,在“尊贤”的道德光环与“伐国”的现实利益之间,此刻国家的核心需求是开疆拓土的军事胜利,李克的将才远胜段干木的清誉。
文侯深谙人性需求层次,明白不同情境下人们(包括他自己)最迫切追求的利益是什么。
千年之后,清末洋务重臣张之洞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提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看似保守的口号,实则是他深刻洞察当时朝野人心、平衡利害的精妙策略。
他深知完全守旧已无法抵御外侮,但全盘西化又必然触动根基,引发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弹,导致改革夭折。
于是,他巧妙地以“卫道”之名,行“变革”之实。
他在《劝学篇》中直言:“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将学习西方科技定位为保全中国根本利益(“体”)的必要手段(“用”)。
这既安抚了清廷中枢的疑虑,又为引进西方技术、创办汉阳铁厂等近代工业扫清了部分思想障碍。
张之洞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精准把握了统治阶层和士大夫群体在时代剧变中的核心关切——维护统治稳定与传统文化主体性。
他找到了新旧利益诉求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魏文侯与张之洞,相隔两千年,却都因透彻理解特定情势下最关键的人性需求——趋何利,避何害——而得以推动事业,名垂青史。
利害,永远是驱动人性最直接、最强大的引擎。
能辨识当下最紧要之利害,并据此调整策略者,方能在复杂环境中觅得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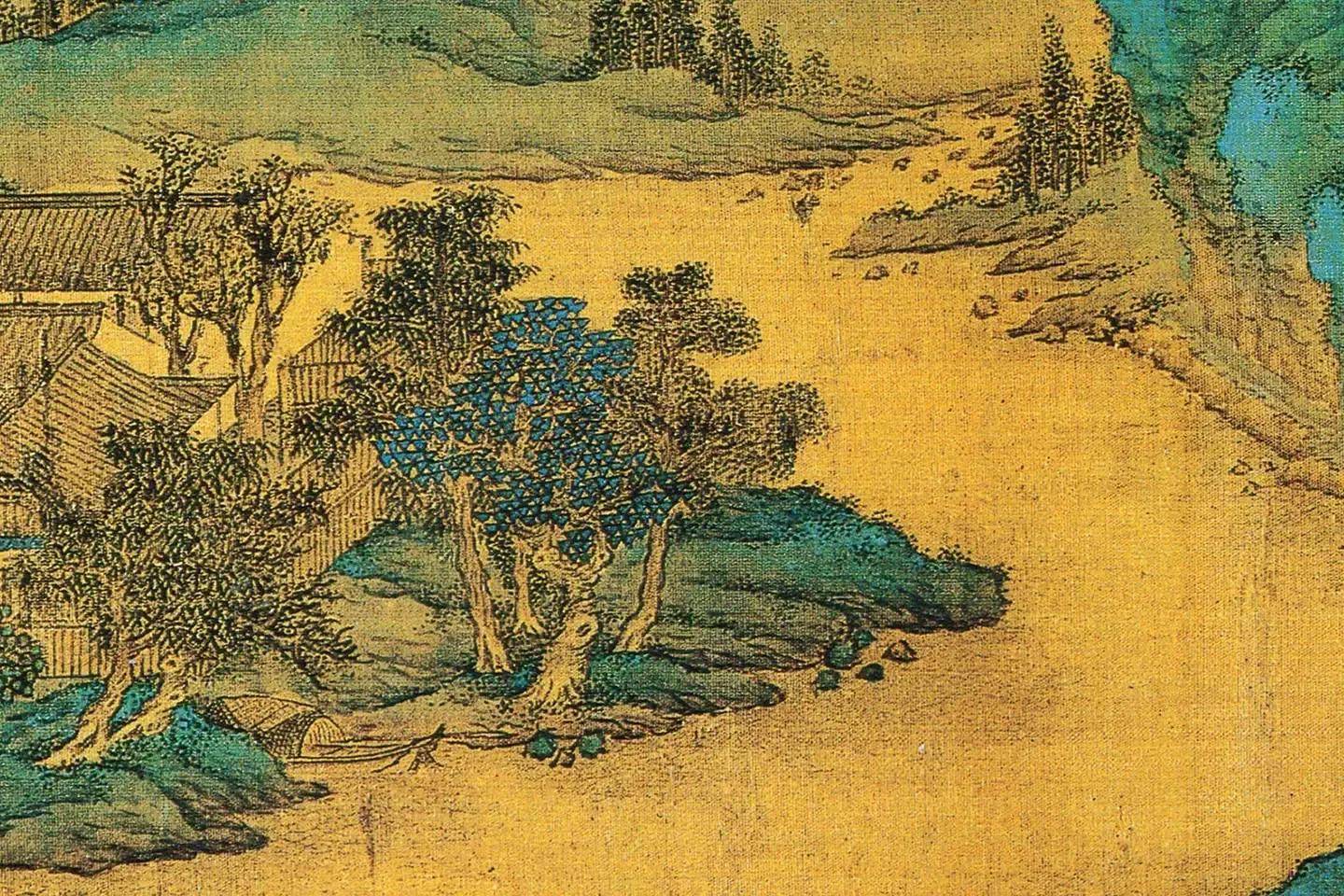
《资治通鉴》卷六记载了长平之战的惨烈前奏。
赵孝成王惑于秦相范雎的反间计,听信了“秦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的虚言。
朝堂之上,蔺相如、赵奢遗孀皆力谏赵括“徒读父书,不知合变”,绝非良将。
然而,赵王眼中只看到赵括谈论兵法的滔滔不绝、意气风发,被其表面的“知兵”假象所迷惑。
他内心深处更渴望一位能带来速胜、提振士气的“名将之后”,以慰藉对秦军压境的恐惧。
结果,赵括代廉颇为将,纸上谈兵终致四十万赵卒被坑杀,赵国元气大伤。
司马光于此痛切指出,赵王之失在于“不察虚实”,被浮言和个人的焦虑蒙蔽了判断。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面对步步紧逼的日寇侵华野心,国民政府高层在战略判断上同样陷入了“虚实之辨”的困境。
部分人沉浸于“国际调停”的幻想,寄希望于列强干涉,甚至低估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决心和疯狂。
淞沪会战期间,“速胜论”一度甚嚣尘上,未能清醒认识到敌我实力在装备、训练、工业基础上的巨大差距。
这种对敌情、我情“实”的误判,对国际援助“虚”的过度期待,导致战略部署出现偏差,虽将士浴血奋战,仍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赵孝成王与抗战初期的某些误判,皆因未能穿透人性中常见的自欺欺人与一厢情愿。
成功者,必具一双冷眼,能剥开浮华、谎言与自我安慰的迷雾,直抵事物坚硬冰冷的本质核心。
洞悉人性之虚妄,方能把握现实之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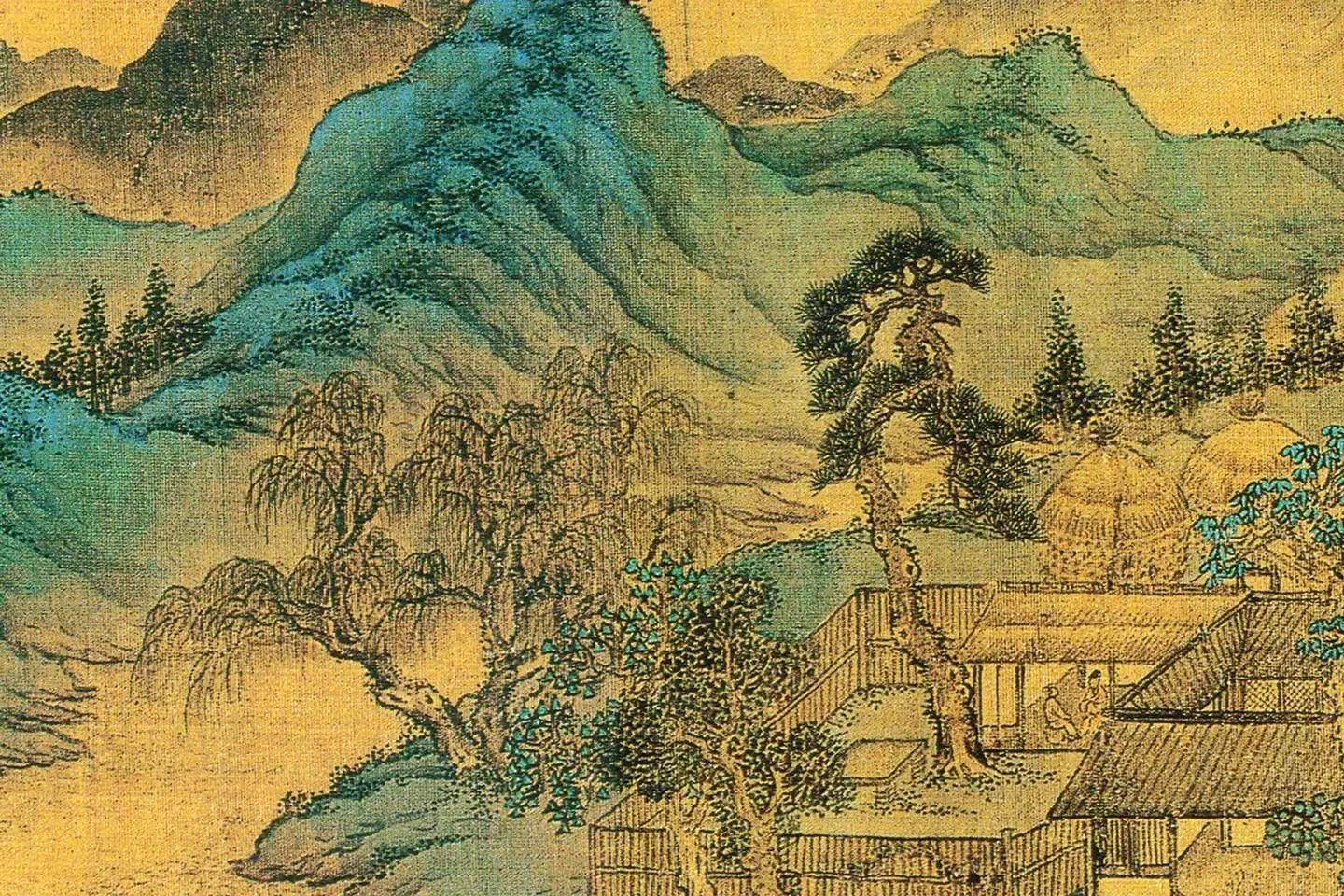
《资治通鉴》汉纪部分,汉宣帝刘询登基后的隐忍堪称典范。
当时权臣霍光辅政,威震朝野,“政事一决于光”。
年轻的宣帝深知霍氏家族势力盘根错节,其本人更对霍光有废立之功心存忌惮。
他选择了极致的“退”:对霍光礼敬有加,言听计从,甚至霍光还政时也坚决推辞,“谦让不受”。
在霍光面前,他表现得毫无主见,甘居幕后。
朝臣私下议论新帝过于柔仁。
然而,宣帝并非懦弱,他深知此时强行争权无异于以卵击石,他在“退”中观察、等待、积蓄。
直至霍光病逝,霍家失去主心骨,且其子弟不法之事渐露,宣帝才以雷霆手段,步步为营,最终将庞大的霍氏集团连根拔起。
司马光评其“能养威重,承大统”,这份在弱势时主动退避、静待时机的智慧,正是基于对权臣人性(贪权、骄纵必致败亡)和自身处境的深刻把握。
近代中国商界巨子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创业史,同样写满了“进退”的智慧。
他们在面粉、纺织业取得巨大成功后,并未盲目扩张。
面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政局动荡、世界经济危机冲击、日资企业挤压等多重困境,他们审时度势,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
果断收缩部分战线,集中力量巩固核心产业,加强内部管理,引进先进技术,甚至不惜关闭部分效益不佳的工厂以保存实力。
这种看似保守的“退”,实则是为了规避风险、蓄积力量。
待形势稍稳,他们又能迅速抓住机遇,实现更大发展。
荣氏企业历经风雨而能基业长青,与其掌舵人深谙“知进知退”的人性化生存法则密不可分。
霍光权倾朝野时的“进”,终招灭族之祸;汉宣帝与荣氏兄弟在特定情境下的“退”,反而成就了长远的“进”。
《资治通鉴》反复昭示:人性常趋“进”而惮“退”,然明者见危于无形,知何时当激流勇进,何时该韬光养晦。
能参透此中玄机者,方能在人生的激流险滩中行稳致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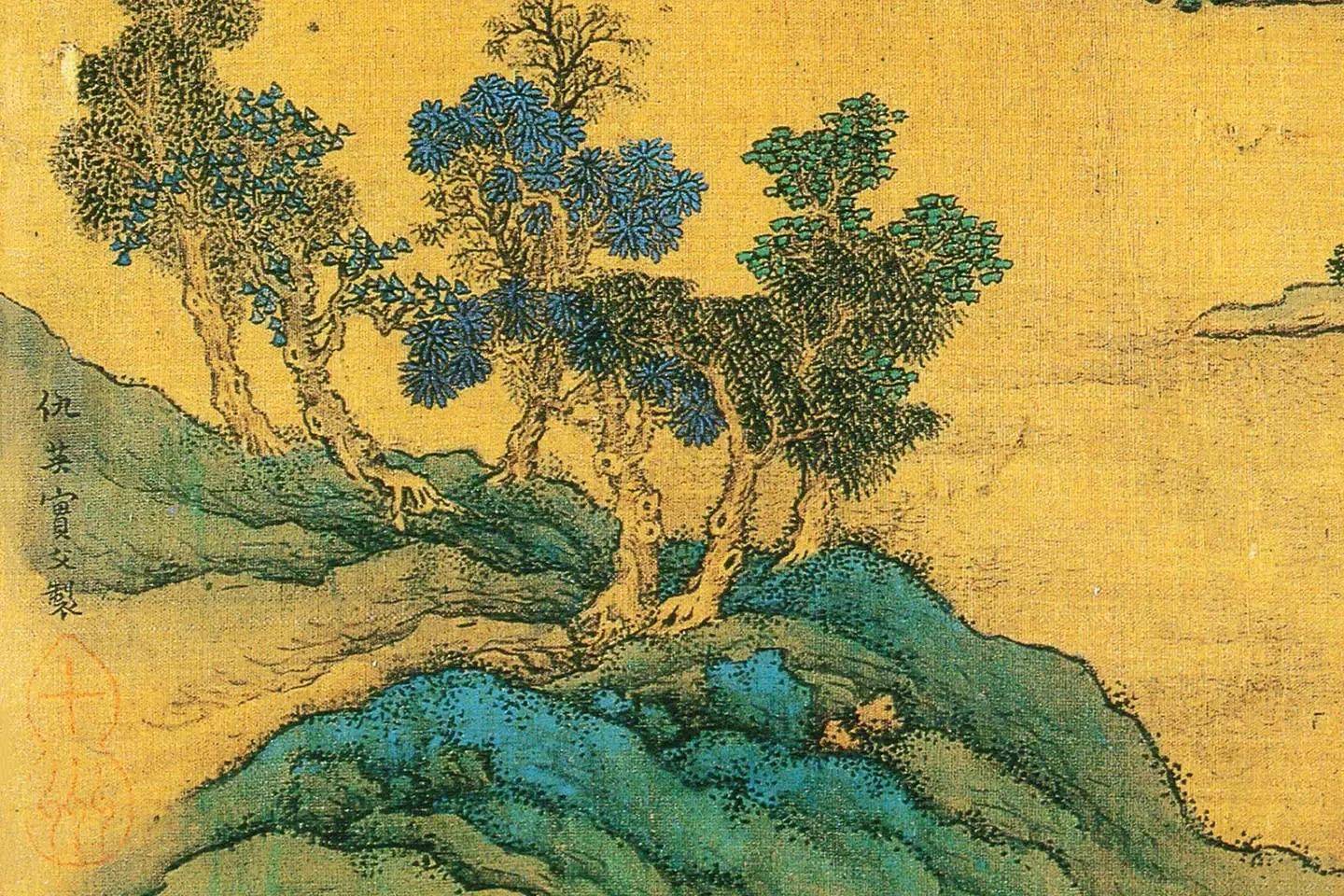
《资治通鉴》如一面巨镜,映照出千年不变的人性底色。
司马光穷其一生,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其核心便是洞察人性在历史棋局中的关键落子。
无论是魏文侯、张之洞对利害的精准拿捏,还是赵王、抗战初期对虚实的误判之痛,抑或汉宣帝、荣氏兄弟在进退间的从容斡旋,都深刻印证了这一点。
成败荣辱的密码,往往就隐藏在“趋利避害”、“慕虚忘实”、“知进难退”这些人性的幽微褶皱之中。
读懂了人性,就读懂了历史的逻辑,也握住了破局当下的钥匙。
故曰:欲成事者,必先察人。
以史为鉴,明心见性,纵使世路崎岖,亦能于人性的迷宫中,寻得那束指引成功的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发表评论 评论 (0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