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言,《资治通鉴》是帝王之镜,更是众生之书。
它记录的不仅是王朝兴衰,更是无数个体在命运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
千年史册翻过,那些能在乱世沉浮中站稳脚跟的人,往往深谙三个朴素的道理:不糊弄,不摆烂,不抱怨。
世事艰难,糊弄终会露馅,摆烂必致沉沦,抱怨徒增烦扰。
唯有直面,方能破局。
他们的故事,穿透纸背,至今回响。

翻开《资治通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正在上演。
智伯的家臣豫让,在主人被赵襄子所杀、头颅被漆为饮器后,陷入了真正的绝境。
国破家亡,主辱臣死,他似乎已无路可走。
然而,豫让没有选择消沉或逃避,他喊出了那句震铄古今的誓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智氏之仇矣!”
为了接近仇人赵襄子,他不惜“漆身为癞,吞炭为哑”,彻底毁掉自己的容貌和声音,行乞于市。
第一次刺杀失败被擒,赵襄子感其义气释放了他。
但豫让并未放弃,更未糊弄自己复仇的决心。
他埋伏在赵襄子必经的桥下,准备第二次刺杀。
命运再次捉弄,他因马惊而暴露。
面对赵襄子“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灭之,而子不为报仇,反委质事智伯”的质问,豫让的回答掷地有声:“范、中行氏以众人遇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遇我,我故以国士报之!”
他自知必死,只求击刺赵襄子之衣以明志,最终伏剑自杀。
在绝对的绝望中,豫让以最惨烈的方式,拒绝向命运摆烂,践行了心中的“义”,虽死犹生。
千年后,在近代中国的困境中,詹天佑的身影同样诠释着拒绝摆烂的精神。
1905年,当清政府决定自力修建京张铁路,面对外国人的嘲笑和复杂险峻的关沟段,詹天佑没有退缩,更没有敷衍塞责。
他带领工程人员,背着标杆、经纬仪,在悬崖峭壁上定点、测绘。
面对八达岭隧道长、工期紧的难题,他创造性地采用了“竖井开凿法”,增加了工作面。
为解决青龙桥附近坡度过大的问题,他匠心独具地设计了“人”字形折返线路。
没有先进设备,就靠人力与智慧。
没有外国专家,就自己摸索攻坚。
他常对助手说:“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
历时四年,这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条干线铁路提前两年通车,粉碎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断言。
詹天佑在技术落后、资源匮乏的绝境中,以科学的态度和顽强的意志,拒绝摆烂,成就了民族铁路事业的丰碑。
绝境,是考验灵魂的熔炉。
糊弄和摆烂,只会让熔炉变成坟墓。
豫让的剑,詹天佑的轨,都在无声地宣告:纵使深渊在前,也要挺直脊梁,一步一个脚印地凿出生路。
真正的强者,不在顺境中显赫,而在深渊里拒绝沉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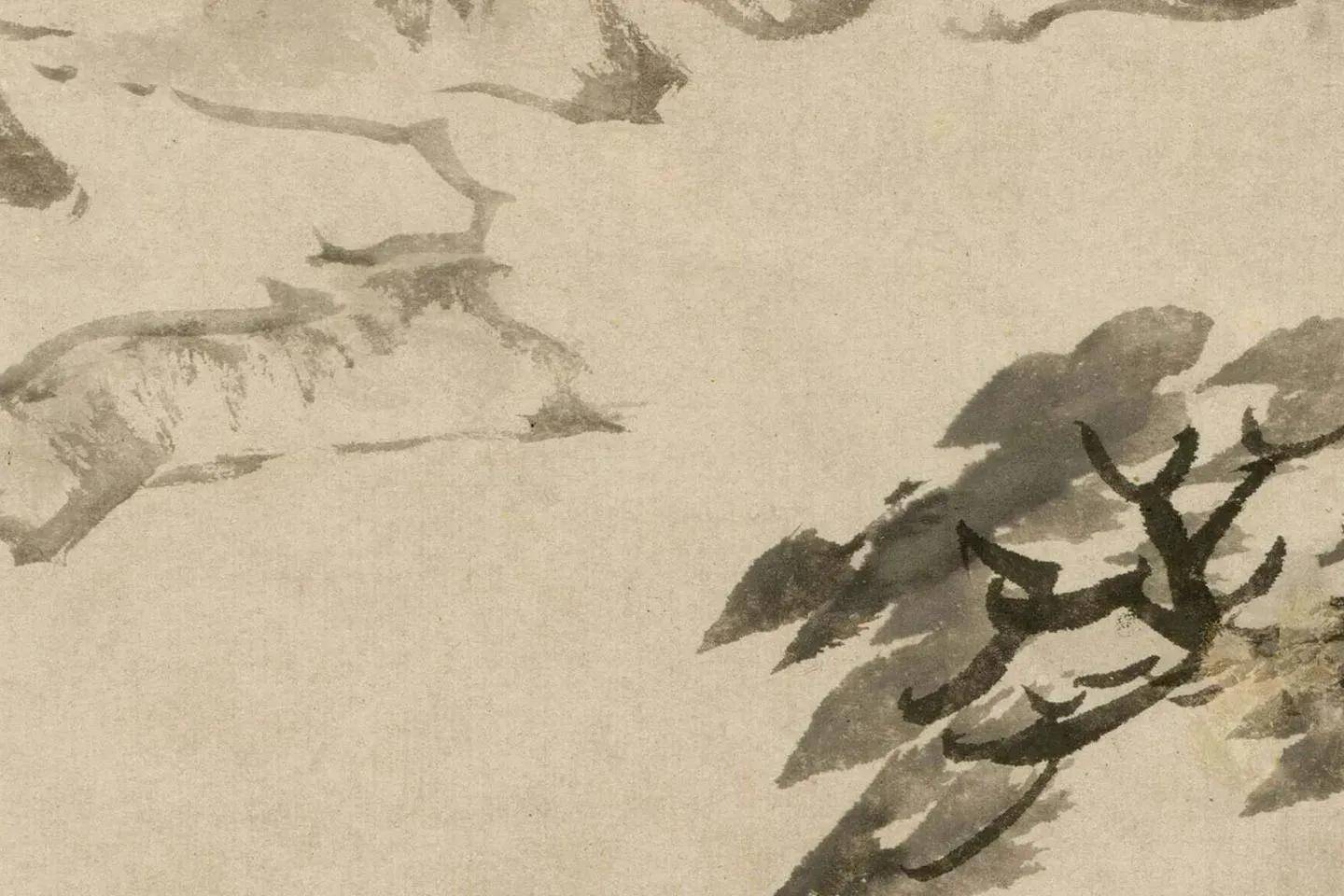
《资治通鉴》卷六记载了战国末年赵国名将李牧的悲剧。
李牧,这位曾大破匈奴、令其十余年不敢近赵边的“军神”,在秦军压境的危难时刻,被赵王迁委以重任,抗击强秦。
他深沟高垒,固守不出,消耗秦军锐气,寻找战机。
他的策略卓有成效,秦将王翦深知李牧不除,灭赵无望。
于是,秦人使出了反间计。
重金收买的赵王宠臣郭开,开始在赵王面前日夜诋毁李牧,诬陷他与副将司马尚意图谋反。
昏聩的赵王迁听信谗言,不加核实,便下令解除李牧兵权,由赵葱和颜聚替代。
当使者手持王命抵达军营时,李牧面临人生最残酷的背叛。
君王不信,佞臣构陷,前线将士的生死存亡系于一线。
《资治通鉴》用冰冷的笔触写道:“李牧不受命。”
他深知临阵易帅乃兵家大忌,赵国危在旦夕。
然而,君命难违,使者催促。
李牧没有选择公开抱怨君王的昏聩,没有斥责郭开的无耻,也没有煽动将士抗命引发内乱。
他选择了最沉默也最刚烈的方式:“牧曰:‘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之,杀匈奴十余万骑…’(此处简述李牧功绩以示其能,非抱怨之词)今王信谗,臣固知赵必亡矣。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然今王疑臣至此,臣亦不敢惜死以误国事。唯愿王察之!”言罢,交出兵符,慨然引剑自刎于军门之前。
李牧用生命承担了责任,至死未发一句对背叛者的怨怼之辞,只留下一声对国家命运的悲叹。
他的死,直接导致了赵军的崩溃和赵国的迅速灭亡。
这份在滔天冤屈与背叛面前强忍悲愤、戒除抱怨、以死明志的担当,令人扼腕,更发人深省。
历史的回音在二十世纪中叶再次响起,主角是钱学森。
当这位世界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家决心返回新中国效力时,遭遇了美国当局的无理阻挠和背叛。
莫须有的罪名扣下,移民局非法拘留,联邦调查局严密监视,长达五年的软禁生活开始。
他的行李被扣押,研究手稿被没收,人身自由被剥夺,甚至时常接到恐吓电话。
面对如此不公的待遇和巨大的精神压力,钱学森没有沉溺于抱怨。
他没有公开指责美国政府的蛮横,也没有在私人信件中过多宣泄愤怒。
他将精力转向了全新的学术领域——工程控制论,在受监控的家中潜心著述。
同时,他利用一切合法途径,机智地与当局周旋,寻求归国之路。
他将求救信写在香烟纸上,夹在给欧洲亲戚的家书中,最终辗转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
在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这封信成为中方要求美方放人的关键证据。
漫长的五年里,钱学森把被背叛的愤懑,化作了深沉的思考和更坚定的归国意志。
他后来回忆那段岁月时说:“我没有时间抱怨,我必须为回去后能做什么做准备。”
1955年,冲破重重阻挠,钱学森终于踏上归途。
他戒除抱怨、专注行动的坚韧,为新中国航天事业奠定了基石。
背叛如同淬毒的冷箭,抱怨则是任由毒液蔓延。
李牧的血,钱学森的忍,都印证了一个道理:遭遇不公,沉溺抱怨只会消耗自己,模糊方向。
真正的智者,会咽下苦涩,将冤屈转化为沉默的力量,或如李牧般以死守责,或如钱学森般砥砺前行,在至暗时刻守护内心的光,等待破局的时机。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记载了中唐名臣李泌的传奇。
安史之乱后的大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局如走马灯般变幻。
李泌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每一次权力更迭都伴随着腥风血雨。
他亲眼目睹宰相杨国忠被乱刀分尸,亲历肃宗听信谗言诛杀建宁王李倓,更在代宗朝因得罪权宦鱼朝恩而被迫归隐。
当德宗因“泾师之变”仓皇出逃奉天,大唐国运悬于一线时,年过六旬的李泌再次应召出山。
面对满目疮痍的江山和猜忌多疑的新君,他没有丝毫糊弄。
他不避嫌怨,力劝德宗与回纥结盟共抗吐蕃,哪怕曾被朝臣攻击“勾结胡虏”。
他洞悉藩镇军阀李怀光的反复无常,直言其“包藏祸心”,坚持调兵防备,最终避免了一场更大叛乱。
当德宗欲废太子另立时,他深夜叩阙,以死相谏:“陛下昔欲废太子,臣不敢言;今太子无罪,陛下奈何听信谗言?若必行此,臣请先死于此阶!”
在波谲云诡的朝堂上,李泌始终以“至诚”立身,以“务实”为政,从不因时局艰危而敷衍塞责,更不为保全富贵而曲意逢迎。
他用一生践行了《资治通鉴》所倡的“为社稷死则死之”,在无常乱世中筑起一道不糊弄的脊梁。
历史的指针拨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
华北平原上,一个叫费孝通的年轻学者,正徒步穿行于炮火与饥馑交织的乡村。
日军铁蹄步步紧逼,学术机构流离失所,研究条件极其恶劣。
许多人劝他暂避海外,或写些应景文章敷衍。
费孝通拒绝了。
他背起行囊,深入江苏吴江的开弦弓村,一住就是两个月。
没有经费,就自掏腰包;没有助手,就独自访谈;白天与农民同吃同住,夜晚在油灯下整理笔记。
轰炸机在头顶轰鸣,他伏在田埂下护住调查手稿;疟疾高烧不退,他仍挣扎着记录婚丧嫁娶的细节。
他对自己说:“若不能真切理解乡土何以破碎,救国便是一句空话。”
一年后,浸润着血汗与诚意的《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的里程碑”。
书中没有一句空喊的口号,只有对蚕丝业凋敝、土地制度僵化的冷静剖析,为中国乡村变革提供了最扎实的注脚。
战火纷飞中,费孝通用双脚丈量苦难,以笔墨解剖真实,绝不因国难当头而降低学术标准,更不为个人安危而糊弄时代赋予的使命。
无常是世间的常态,糊弄是弱者的盾牌。
李泌的谏言,费孝通的笔,都刺穿了这面虚幻的盾。
他们在惊涛骇浪中锚定一点:事无论大小,境无论顺逆,当为处必竭其力,当言处必尽其诚。
不糊弄,是对无常最有力的回应,是在混沌中守住的那方清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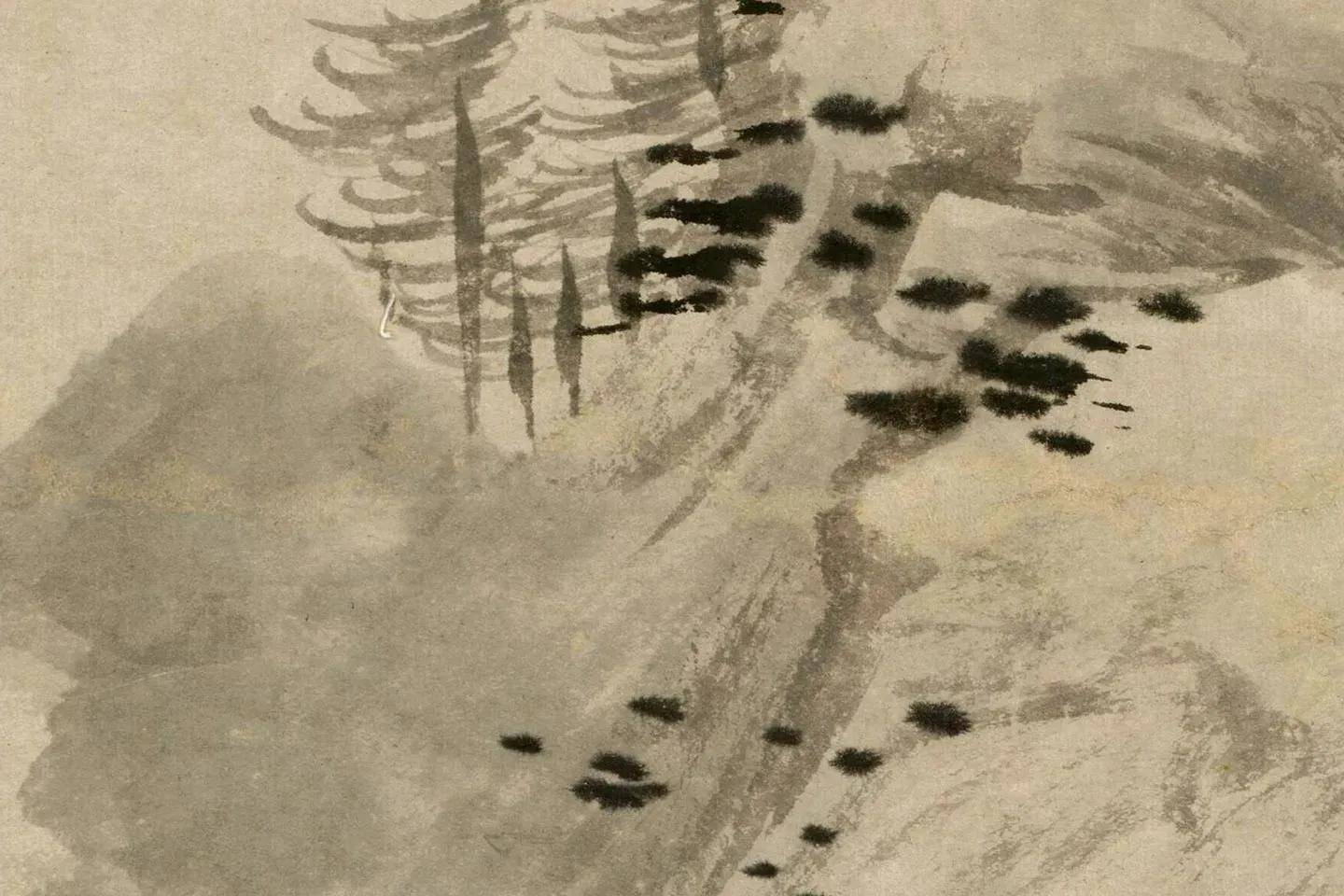
千年青史如镜,照见多少兴亡。
《资治通鉴》里那些不糊弄、不摆烂、不抱怨的灵魂,穿透尘埃,依旧铮铮作响。
豫让的剑光,李牧的沉默,李泌的诤言;詹天佑的轨,钱学森的稿,费孝通的笔……他们以血肉之躯,在各自的绝境中刻下“担当”二字。
世事从无坦途,糊弄终露马脚,摆烂必致深渊,抱怨徒增枷锁。
唯以不欺暗室的诚,不坠青云的志,不怨天尤人的韧,方能在洪流中站稳。
看透无常而不敷衍,历尽背叛而不沉沦,身处绝境而不放弃——这便是《资治通鉴》留给后世最硬的骨头,最亮的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发表评论 评论 (5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