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言:“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信义其本也。”
一部《资治通鉴》,写尽王朝兴衰,亦刻下无数因失信而倾覆的轨迹。
商道无信,则财路断绝;基业失信,则宏图崩塌。
尘埃落定处,唯信义二字,重逾千钧。

《资治通鉴》载,战国魏文侯与掌管山泽的小吏虞人约定某日一同狩猎。
到了那天,文侯正与群臣饮酒作乐,天又下起大雨。
他兴致正浓,却立即起身,命人备车前往郊野。
左右不解:“饮酒如此快活,天又下雨,君侯要去哪里?”
文侯答:“我与虞人有约,虽然快乐,怎能不守约定?”
于是亲自驱车前去,告知虞人因雨取消狩猎。
魏国群臣及百姓闻之,皆叹服文侯之信。
这份对微末小吏的诚信,筑起了魏国强盛的基石,四方贤才闻风而至。
信诺,是看不见的基石,却能撑起最宏伟的殿堂。
时间流转至清末民初,南通张謇怀抱“实业救国”之志。
他创办大生纱厂,资金捉襟见肘时,曾向上海钱庄借贷。
约定还款之日,恰逢年关,天寒地冻,运河封航。
陆路运输成本陡增数倍。
若延迟还款,钱庄未必深究。
但张謇认定,商誉重于千金。
他毅然选择花费巨资,组织人力畜力,日夜兼程,硬是将沉重的银元如期运抵上海。
钱庄掌柜目睹此景,深受震撼。
“张謇一诺,价值连城”的美誉不胫而走。
此后,大生纱厂在商海中融资扩产,畅通无阻。
银元叮当响,信用当钱花。
张謇以生命践行的信诺,为他庞大的实业帝国铺平了道路。
商道漫漫,信为舟楫。
能载重,亦能致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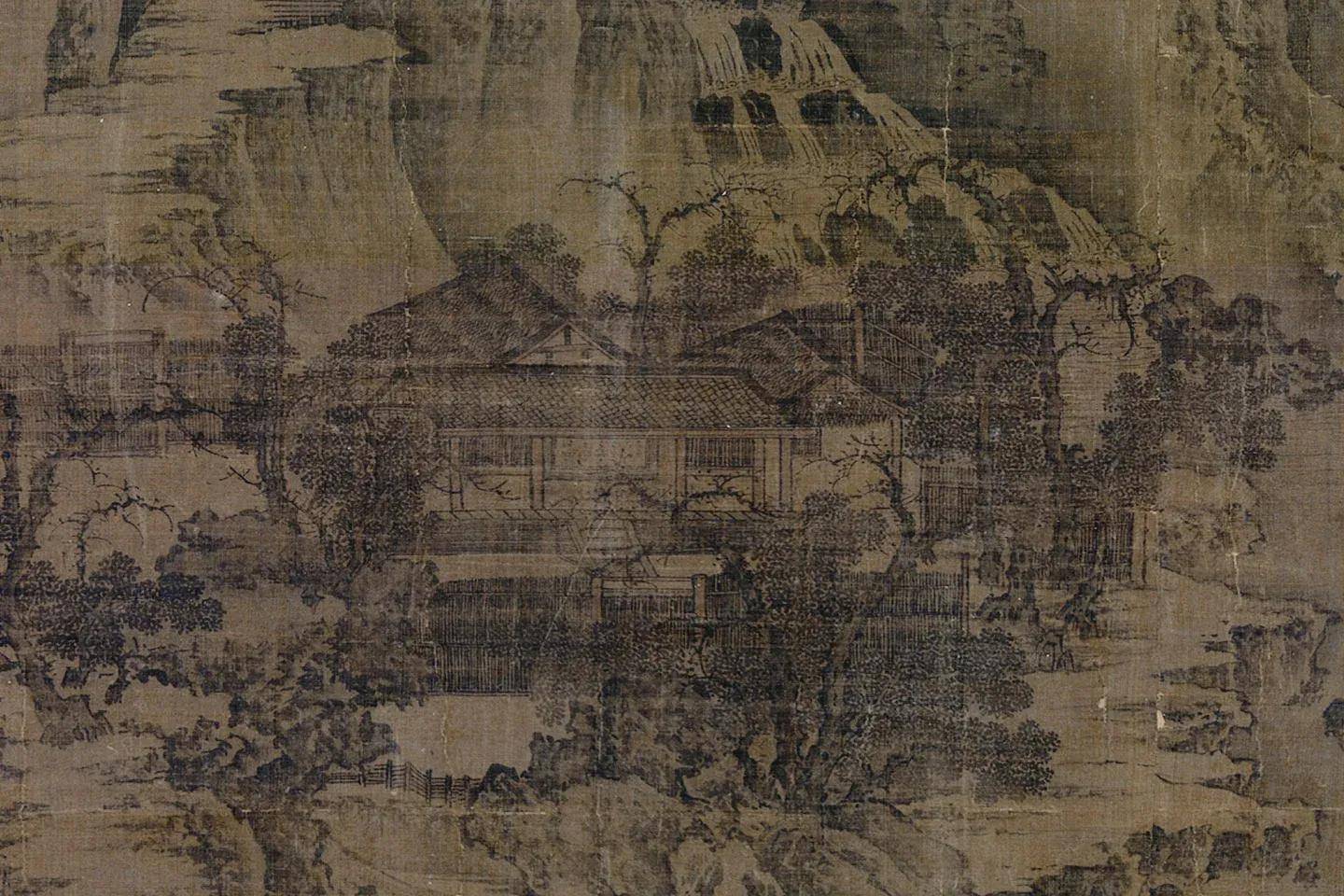
《资治通鉴》中,官渡之战曹操以弱胜强,缴获大量文件。
其中不乏己方官员与袁绍暗通款曲的书信。
左右皆言:“当按名收捕,以绝后患。”
曹操却下令,不必检视,尽数焚毁。
火光熊熊,照亮他沉静的面容:“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他人乎?” 此一举,非仅宽宥,更在立信。
他深知,穷究必致人人自危,猜忌蔓延,人心离散,则根基动摇。
灰烬飘散处,人心归附时。
信用崩塌的裂痕,往往始于一次看似微小的背弃。
反观近世,1985年,青岛电冰箱总厂(海尔前身)仓库里,76台有瑕疵的“瑞雪”牌冰箱静静躺着。
彼时物资紧俏,冰箱凭票供应,次品亦不愁销路。
厂长张瑞敏面对职工不解,抡起大锤,亲手砸毁了第一台。
“今天不砸了这些冰箱,明天市场就会砸了我们的工厂!”
锤声震耳,砸碎了短视的侥幸,也砸醒了全员的质量与信誉意识。
若当时选择将瑕疵品流入市场,换取蝇头小利,何来日后“海尔中国造”的金字招牌?
毁诺易如反掌,重建难若登天。
堤坝溃于蚁穴,信誉毁于一念。
守不住那份契约精神,再辉煌的楼阁,也终将沦为废墟。

《资治通鉴》唐纪中,唐德宗猜忌之心尤重。 名将李晟收复长安,功勋卓著,却反遭帝王深深疑惧。
德宗听信谗言,疑其拥兵自重。
先是不许李晟擅杀违纪宦官,削其威信。
后又借吐蕃离间之计,解除了李晟的兵权,将其明升暗降,闲置京城。
李晟“常感泣,目为之肿”,忠臣良将,心寒齿冷。
朝野见此,忠直之士噤若寒蝉,藩镇将领愈发骄横跋扈。
君臣离心离德,朝廷威信扫地。
德宗一朝,叛乱频仍,国势日颓,其根源,何尝不在君王自毁长城、失信于股肱? 君臣无信,则国本动摇。
近代中国,实业巨子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怀抱实业救国之热忱,倾力发展民族工业。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日寇威逼利诱,企图攫取其庞大的申新纱厂。
荣氏兄弟坚守民族大义,严词拒绝合作,宁可将工厂内迁或炸毁,亦不让资敌。
其拳拳爱国之心,天地可鉴。
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却以“敌产”为名,强行“接收”荣氏企业,横征暴敛,几近掠夺。
此无异于对民族企业家爱国赤诚的背弃与践踏。
荣氏企业元气大伤,无数民族工商业者亦为之寒心。
政府失信于民,失义于商,其统治根基的溃烂,已可预见。
庙堂失信,则万民离心。
纵有金城汤池,亦难逃土崩瓦解之局。

《资治通鉴》如镜,映照千年兴亡,皆系于“信”字经纬。
商道如江湖,信是舟,无信寸步难行。
基业似广厦,信为基,无信顷刻倾覆。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无信不立。
纵使世事翻云覆雨,守心如一诺。
心灯长明,则前路自有光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发表评论 评论 (6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