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百年新诗史,诸多著名论战深刻呈现并塑造了诗歌的发展脉络与时代审美。无论发轫之初《晶报》与胡适关于新诗形式的探讨,周作人、康白情与朱自清围绕诗歌“精神贵族”与“平民化”定位的争论,还是“盘峰论争”中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分野,乃至北岛与王家新翻译理念之争。这些论战虽立场针锋相对,却共同推动了诗歌艺术的演进,参与者也因此在新诗史上确立了各自的地位。
近日,唐小林与余秀华的论战持续发酵,网络热度居高不下。我将两人的文章《余秀华,当代诗坛的巨大泡沫》与《唐小林,男人的泡沫》悉数发布于朋友圈,供友人自行判断。
平心而论,余秀华早期部分诗歌确有其价值,如《月光落在左手上》等作品展现了独特的诗艺探索与疼痛美学,其底层书写亦具社会意义。整体而言,早期诗作可圈可点。她对邬霞的写作水准的某些评价,并非全无道理。有个诗人跟帖“要说余秀华的泡沫,那算小了”,也认可。
然而,余秀华最引人注目的,恰是其“诗”与“人”的剧烈割裂。这种割裂,映射了其创作人格与公共行为的巨大反差,也标志着余秀华从“横店村农妇诗人”向“流量诗人”的蜕变。后期创作困境的意象重复,依赖情感宣泄等,或许正是这种身份转化土壤催生的结果,致使苦难叙事滑向消费符号。回到论战本身,双方或大或小的偏执都有,有些主观的、八卦的,包括余秀华的语言粗暴,唐小林的断章取义、选择性忽视与盖棺论定等,就不多说了,让人意外的有两点:
其一,在回应唐小林批评的网文中,余秀华对唐小林指出的诅咒“邬霞‘小心两个女儿被撞死!’”一事避而不谈,甚至未作任何形式的道歉。这在以往严肃、富有建设性的文坛论战中实属罕见,也与余秀华诗歌中“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所展现的悲悯、脆弱形象构成巨大反差。究其本质,这已远超理性公共讨论的范畴,纯属恶意攻击,且公然践踏了文明底线与法律边界。诚然,事件起因于邬霞率先嘲讽余秀华“摇头晃脑、口齿不清”,余秀华随后以“以色示人”回击,双方言辞均不光彩。然而,无论骂战如何升级,将战火引向无辜者(尤其是孩童)的行为,于情、于理、于法皆难容。余秀华似乎并未意识到其言论的严重性。若当事人选择追究并固定证据,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余秀华极可能面临公开道歉、赔偿乃至行政拘留的处罚。鉴于其言论传播影响广泛(点击率及影响远超一般标准),情节已属严重,甚至可能触及《民法典》第1024条(名誉权)与《刑法》第246条(侮辱罪、诽谤罪)规定的刑事责任。倘若被诅咒的孩子中有一人未成年且因此遭受心理创伤,其法律后果将更为沉重。
其二,余秀华在质问唐小林时,将对其作品《且在人间》的文学批评,偷换为对体制的攻击:“你说我的小说不够发表水平?那你讲清楚标准是什么!《收获》是国刊,归zxb管理吧?你质疑《收获》就是在怀疑zxb,就是在怀疑我d的正确性吗?”这种言论令人愕然:一个以“高昂着头”自诩的诗人,竟熟练运用借势打压、构陷异见的伎俩?难道批评一片叶子,就等于否定整座森林?这在逻辑上犯了典型的“归因谬误”,在推理上更是“罪恶关联”的范本。而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这套“上纲上线”的手法,曾让多少人闻之色变。
文学评论界常探讨“名家”与“大家”的分野,其核心差异不仅在于才情技艺,更在于精神格局与人文底蕴的深度。名家或可凭借惊艳之作横空出世,占据一时风骚;而大家则需在此基础上,持续贡献具有超越性的精品力作,展现出相对稳定的创作高度与精神向度。这种持续性与超越性,正是其精神格局稳固、人文涵养深厚的体现。发布在朋友圈文章的留言不少,北大何博士在跟帖中说到:“余秀华因病患,因挚爱的缺失,葆有一颗敏感的心,但也因此而充满扭曲与怨恨,出自底层所沾染的言语恶意,在她的诗性与率性中纠结交错,她战胜不了痛苦,就不能升华到人文与神性层面。最终,其诗歌在审美上只能停留在俗曲与村妇的层面。” 何博士捕捉到了余秀华创作中“扭曲与怨恨”的根源及其未能将个体痛苦升华为普世救赎的创作瓶颈,这一点颇具洞见。然而,其将余秀华诗歌审美定位为“俗曲与村妇”的说法,似乎有所偏颇。更重要的是,何博士将余秀华现实中的部分言行也纳入“率性”范畴,这与我的观察略有分歧。正如前文所析,余秀华的核心问题在于“诗”与“人”的巨大分裂:其诗歌文本中展现的“率性”确乎是其艺术表达的重要特质,但现实中的诸多戾气言行,绝非“率性”所能解释或开脱,其本质是对他人基本尊严的漠视与践踏,“率性”不应成为突破公序良俗和法律边界的遮羞布,“率性”的终点更不应该是他者的坟墓。
有研究者指出,唐小林虽然有祛魅与戳穿文坛虚假繁荣的一面,但其批评方法中存在的某些缺陷——特别是其‘非此即彼’的极端化倾向和对文本整体性的忽视,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其批评的有效性与学理深度。这种带有对抗性色彩的话语,固然能快速聚焦、刺破文坛沉疴,但也容易将复杂的文学现象压缩为二元对立的是非题。这不仅可能损害文艺批评本应具备的理性探讨空间和建设性价值,也在客观上为网络舆论场注入了非理性的发酵因子。这种局限,与其说是个人风格的偏差,不如说是对当前文坛某些痼疾的一种激进但失焦的反弹。
鲁迅早已断言“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网络时代的“崇低美学”虽大行其道,但诅咒孩童、人身攻击等行径已僭越文明底线,令所有参与者尽失尊严,并暴露了使用者的理性无能与语言无能,纵使当下坐拥流量暴利,收割如潮打赏,于新诗建设不过平添呱噪;对诗人自身,无异于饮鸩止渴。当时间的长镜显影,一切粉饰都会剥落,唯余诗性尊严丧失后的狼藉。也唯有时间,终将泡沫与真金分离。
这种扣帽子、人身攻击、诅咒的网络骂战模式,借助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即时性、情绪煽动性,裹挟着资本助力与算法助推,严重挤压了理性讨论的空间,使批评沦为骂战工具,让诗歌沦为八卦注脚,对文学生态造成了巨大伤害,文学界对此必须给与足够重视和高度警觉。
当谩骂已突破文学批评的底线,制度性的回应刻不容缓,可借鉴欧美文学界“恶意批评”的界定机制,适时推出《网络文学批评伦理公约》,以抵制骂战经济对文学生态的侵蚀,重塑批评的敬畏心,重建批评伦理。同时,这也需要文明社会与清醒人群的共同抵制,并敦促尽快落实平台监管责任,建立行业公约,对涉及人身威胁、恶意诅咒与政治构陷的内容及时熔断。否则,若纵容这种暴力文化,听之任之,人人都有可能被反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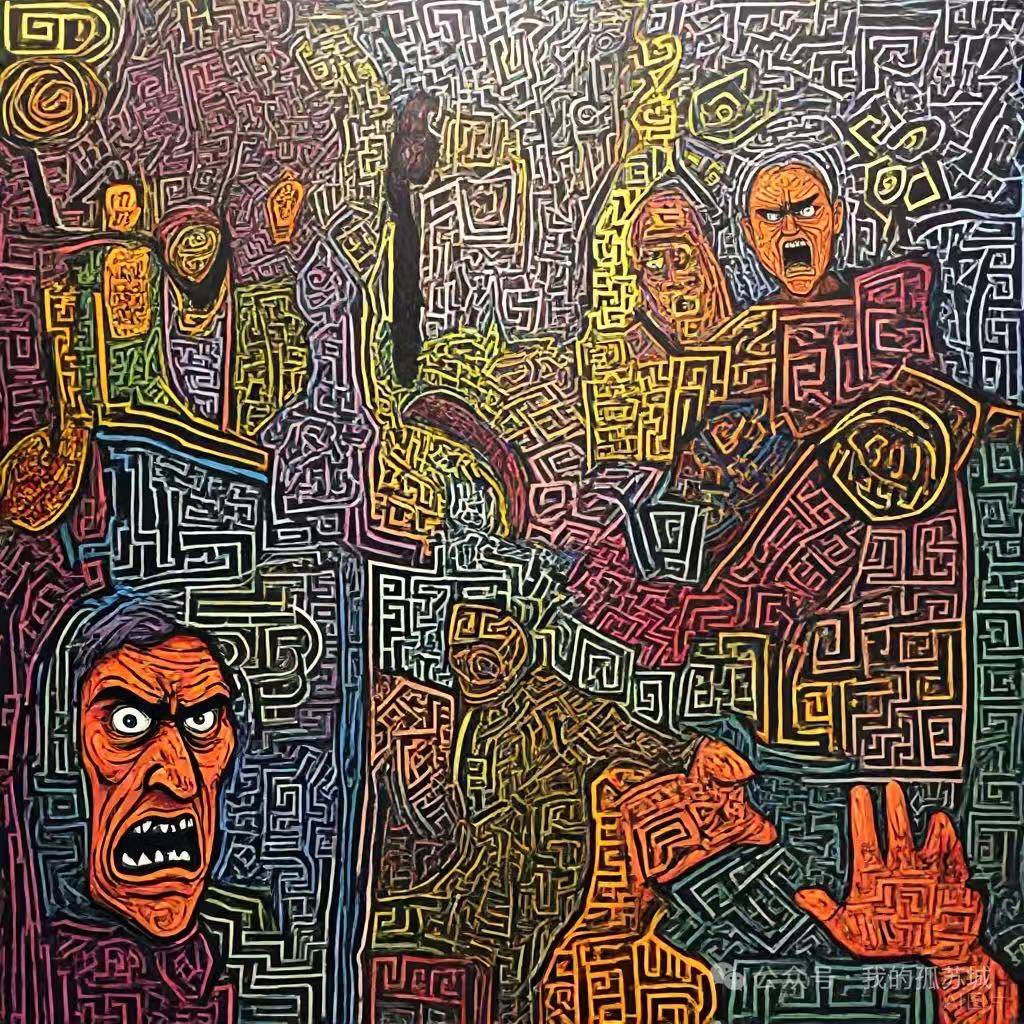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苏忠,作家,诗人,出版诗集、散文集、长篇小说等十部。







发表评论 评论 (3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