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钱江湾

北宋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写下《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中“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的诗句,恰似一根红线,贯穿了他与苏辙四十余载诗文唱和的人生轨迹。自眉山年少时携手赴京,到中年辗转八州、贬途隔山隔水,再到暮年相望泪眼婆娑,兄弟二人以诗词为舟,在宦海沉浮与岁月流转中,载着“风雨对床眠”的初心,藏着血浓于水的牵挂,将千年兄弟情沉淀为最动人的人间范本与文学丰碑。

一、少年壮志:渑池飞鸿踏雪泥,比翼共赴青云路
嘉祐元年,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十九岁的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辞别眉山,踏上赴京赶考的征途。途经渑池,兄弟二人寄宿僧舍,随性题诗于壁。那时候不过是少年意气的率性留痕,却意外开启了一生唱和的序幕。
嘉祐六年,苏轼赴凤翔府任签判,苏辙送至郑州挥别。归途念及渑池旧事,苏辙回到京城后写下《怀渑池寄子瞻兄》:“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骓马但鸣嘶。”诗中“怕雪泥”的牵挂、“壁共题”的追忆,满是少年初历离别时的惦念,字里行间藏着“致君尧舜上”的共同壮志,即便依依惜别,亦对未来满怀憧憬。

苏轼收诗后挥笔作答《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相较于弟弟的细腻怀旧,苏轼的和诗多了几分意境恣逸与通透哲思。
人生漂泊无定,就像飞翔的鸿雁偶然在雪泥上留下爪印,鸿雁飞去后,谁还会计较爪印留在东边还是西边?“飞鸿踏雪泥”的妙喻,既预判了仕途的未知,也透着对世事无常的坦然。那些旅途中的艰辛,那些与弟弟并肩走过的崎岖,早已镌刻进记忆深处。

这组唱和诗无惊天豪情,却藏着少年兄弟的灵犀默契。他们那时或许未曾料想,“鸿飞那复计东西”会成为半生写照,但僧舍中“风雨对床眠”的约定已然生根:待功成名就,便归隐田园,共听风雨、同卧闲叙。这份初心,成了此后漫长漂泊中最温暖的精神慰藉。
二、中年患难:从黄州到儋州,隔山隔水亦相依
黄州岁月,苏轼“躬耕东坡,筑室雪堂”,清贫中仍笔耕不辍。元丰六年,南堂新葺而成,他即景抒怀,写下《南堂五首》其二:“暮年眼力嗟犹在,多病颠毛却未华。故作明窗书小字,更开幽室养丹砂。”意思是我虽已至暮年,庆幸眼力还不错;常年多病,鬓发却未曾花白。特意开明亮的窗户细写小字,又辟幽静的房间炼制丹砂,享受这份清静,诗中尽显物我两忘的清虚心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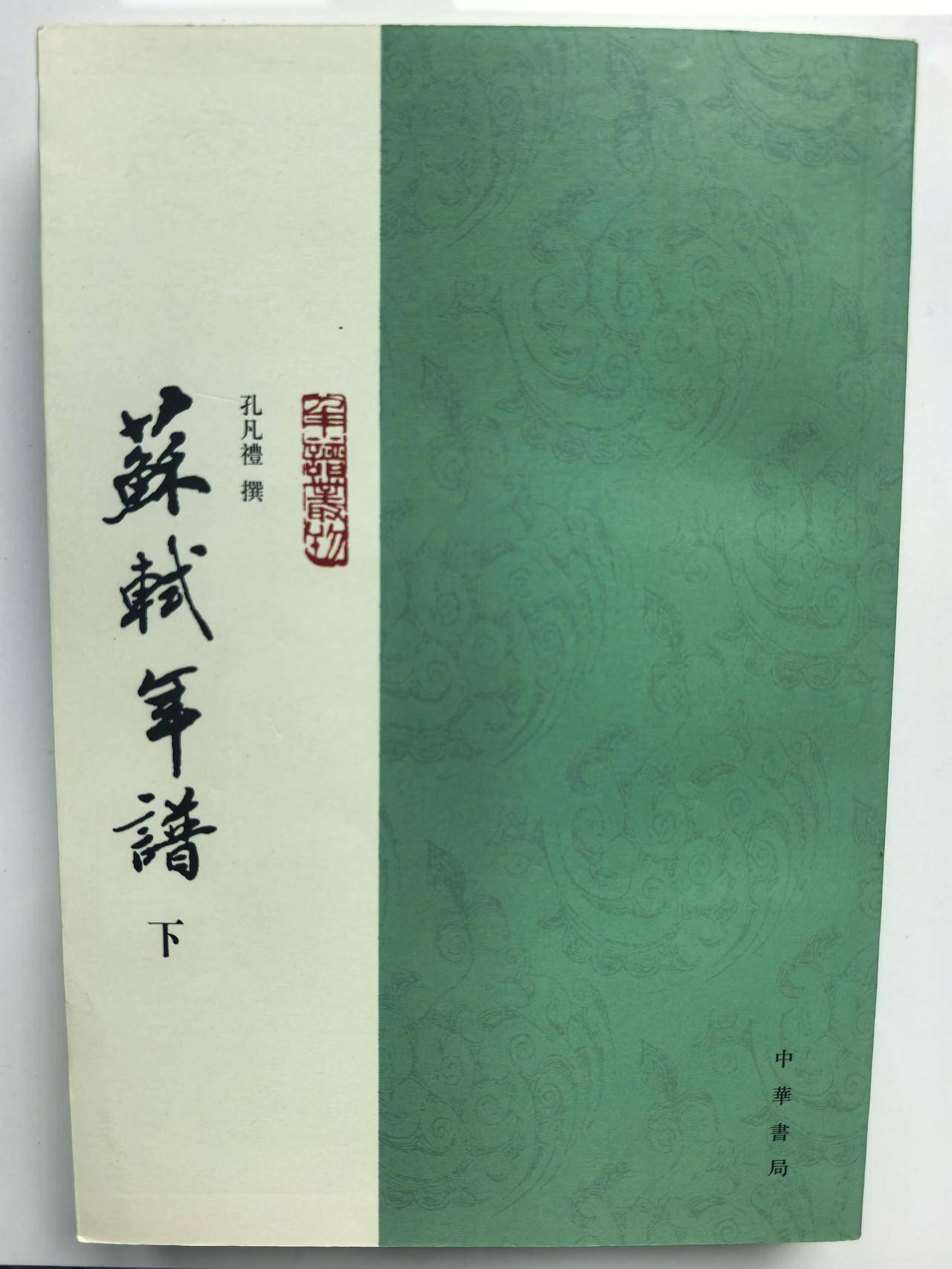
苏辙得悉兄长境况,写下《次韵子瞻临皋新葺南堂五绝·其二》:“旅食三年已是家,堂成非陋亦非华。何方道士知人意,授与炉中一粒砂。”诗中透露出温馨而略带伤感的情绪,既表达了对兄弟安稳生活的渴望,也暗含对过往漂泊生涯的感慨。
许多人熟知苏轼写于密州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的副标题是“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鲜有人知,苏辙接到兄长寄来的中秋词后,所写的和作《次韵子瞻中秋见寄》:“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何时共携手,更把酒杯浮。”意思是我们离别已熬过七个中秋,去年此刻你在东武,我在异地,何时才能再度携手举杯畅饮?苏轼以浪漫驰骋的想象抒怀,苏辙则以冷静现实的笔触,朴素地表达了聚少离多的感慨与重逢的期盼,情感深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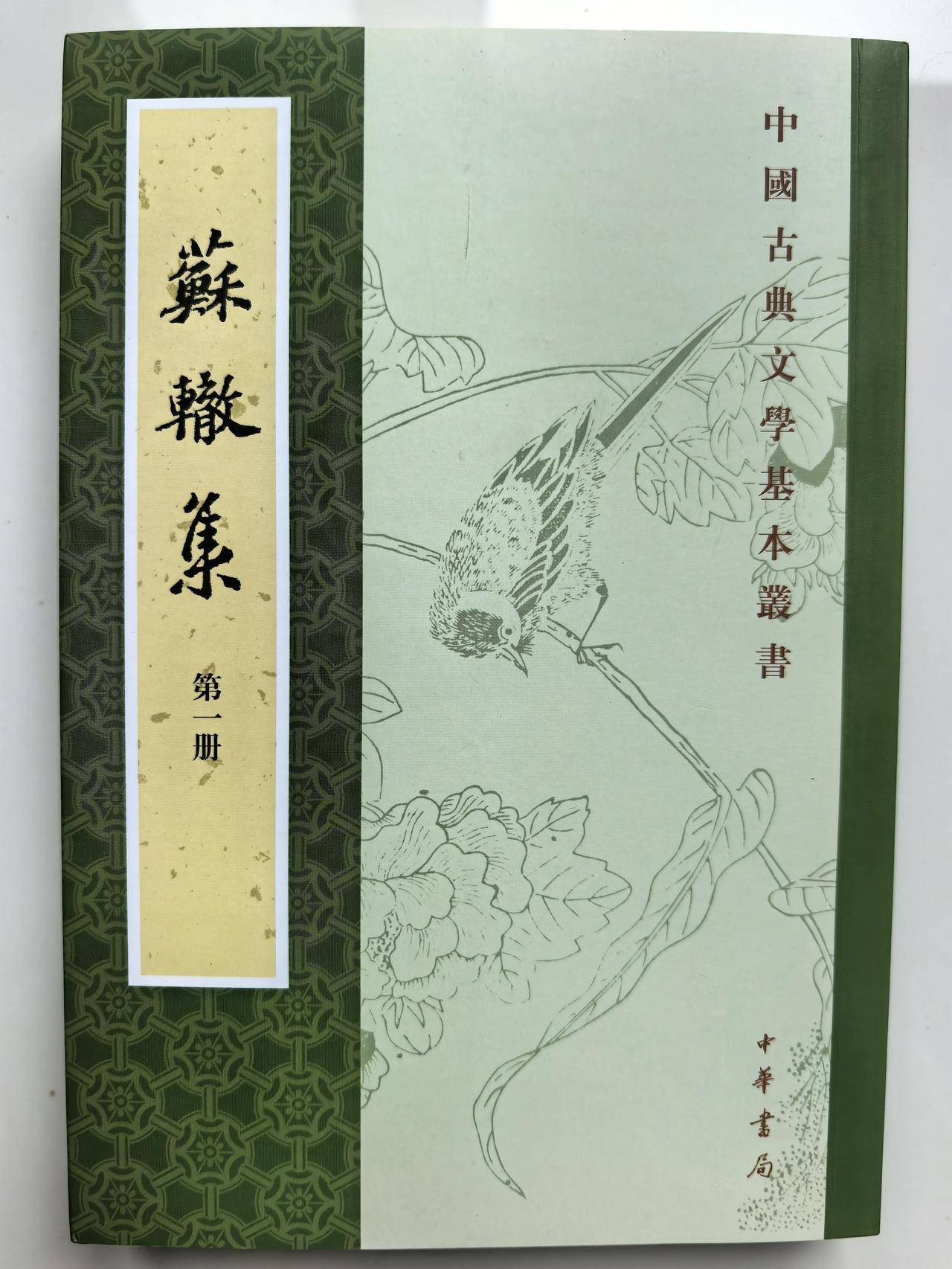
绍圣元年新党执政,苏轼再贬惠州。岭南生活艰难,他对子由的牵挂却从未稍减,作《寄子由》以报平安:“厌暑多应一向慵,银钩秀句益疏通。也知堆案文书满,未暇开轩砚墨浓。湖面新荷空照水,城头高柳漫摇风。吏曹不是尊贤事,谁把前言语化工。” 诗中刻意描摹闲适场景,实则藏着怕弟弟担忧的良苦用心。
苏辙深谙兄长深意,在《次韵子瞻生日见寄》中相慰:“日月中人照与芬,心虚虑尽气则薰。彤霞点空来群群,精诚上彻天无云。”他在诗中称赞兄长“内心澄澈、思虑尽消、气息如兰”,表达了对其才华与人品的敬仰祝福,也透着自身的豪迈情怀。他时常托人寄送衣物药品,苏轼收到后自我调侃:“病中得子由书,寄药一囊,慰我以不死”,寥寥数字,尽是收到牵挂时的安心与感动。

元符元年,贬谪再升级:苏轼赴儋州,苏辙往雷州。茫茫大海隔断去路,却隔不断兄弟情。苏轼到儋州后,回忆渡海前兄弟同遭贬谪的心境,写下《吾谪海南子由雷州作此诗示之》:“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海南与雷州隔着茫茫云海,遥遥相望,上天或许要我将忠义之心留在这偏远之地。将来谁编写地理志,海南万里之地,定会是我真正的故乡。诗中饱含隔海思念,更展现了逆境中的乐观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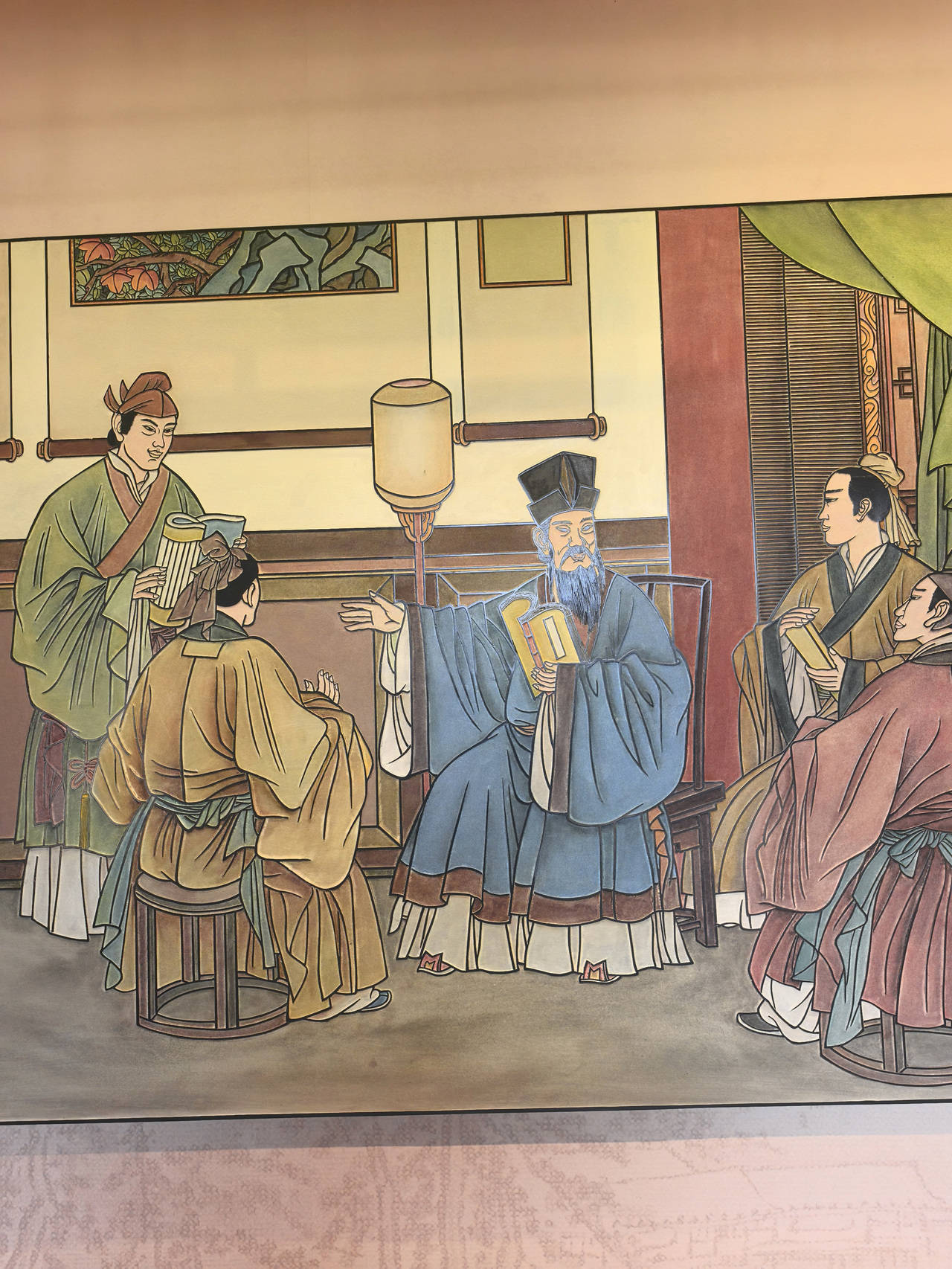
记挂着苏轼困顿的生活,苏辙倾尽积蓄托人寄送,苏轼深为感动。元符三年,他作《过海得子由书》答谢:“经过废来久,有弟忽相求。门外三竿日,江关一叶秋。萧疏悲白发,漫浪散穷愁。世事江声外,吾生幸自休。”诗中描绘秋日苍凉景象,抒发对世事的超脱之情。这份情谊早已超越寻常兄弟情,成为彼此活下去的勇气。
三、风雨对床:一生情一杯酒,唱和无尽照初心
元符三年大赦天下,苏轼得以北归,苏辙也复职为“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宫”,遭永州、岳州安置。兄弟俩雷州送别后,终未能再见。次年七月,苏轼在常州病逝。苏辙遵兄长遗言,将其安葬于河南郏县小峨眉山。墓前,他痛哭写下《祭亡兄端明文》:“手足之爱,平生一人。启手无言,时惟我思。号呼不闻,泣血至地。” 悲恸之中,满是对“风雨对床”约定终成泡影的无尽怅惘。

苏轼晚年极崇陶渊明,写下诸多和陶诗,仿佛与百年前的陶令隔空唱和。他不仅自己唱和,在海南时还邀请苏辙一同追和陶渊明诗作,并寄去《和渊明归去来》:“归去来兮,请终老于斯游。我先人之弊庐,复舍此而焉求?均海南与漠北,挈往来而无忧。……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诗。赋《归来》之清引,我其后身盖无疑。”
那时苏辙从雷州再贬循州,未能及时与兄长同作。苏轼离世后,苏辙整理其遗著,每读旧作便泪如雨下,特意作《和子瞻归去来词(并引)》解释:“昔予谪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渊明归去来》之篇要予同作,时予方再迁龙川,未暇也。”随后,他含悲写下《追和轼归去来词》:“……归去来兮,世无斯人谁与游?斯人不朽惟知时。时不我知谁为留,岁云往矣今何之?”他赞扬兄长睿智“知时”且“不朽”,悲叹哲人已逝、形影相吊,情感沉痛。在闲居颍川的最后几年,苏辙唯有以追和兄长诗作的方式,延续兄弟间的精神共鸣,践行“世世为兄弟”的诺言,让这份情谊在时光中绵延不绝。

纵观二苏一生,从少年渑池唱和,到中年患难互慰,再到暮年贬途相望,诗词唱和始终围绕“风雨对床眠”的初心。唐代诗人韦应物“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的诗句,一直伴随兄弟俩,成为漂泊岁月里的精神灯塔。有人粗略统计,仅诗词唱和(不含文章书信),兄弟二人便近200首。毫不夸张地说,凡是子瞻欣赏过的山河名胜、书作名画,子由无不在异地“神游”或“次韵”相和。二苏的唱和诗,早已超越文学作品的范畴,成为兄弟情的见证与载体,每一首都是心灵对话,每一次唱和都是情感共鸣,以诗词为桥,跨越山海阻隔,抵御宦海险恶,将“兄弟”二字诠释得淋漓尽致。

如今翻阅苏轼苏辙兄弟文集,细细品读这些诗作,仍能感受到穿越千年的感动。正如周华健在《朋友》中所唱的:“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苏轼与苏辙这对“千年第一兄弟”,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兄弟情,是雪中送炭的扶持,是跨越山海的守望,是细水长流的牵挂。“风雨对床四十秋”,这份情藏在“飞鸿踏雪泥”的哲思里,藏在“与君世世为兄弟”的誓言里,藏在“天边同是飘零客”的相慰里,历经岁月沧桑依然熠熠生辉,温暖着每一个读懂它的人。








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