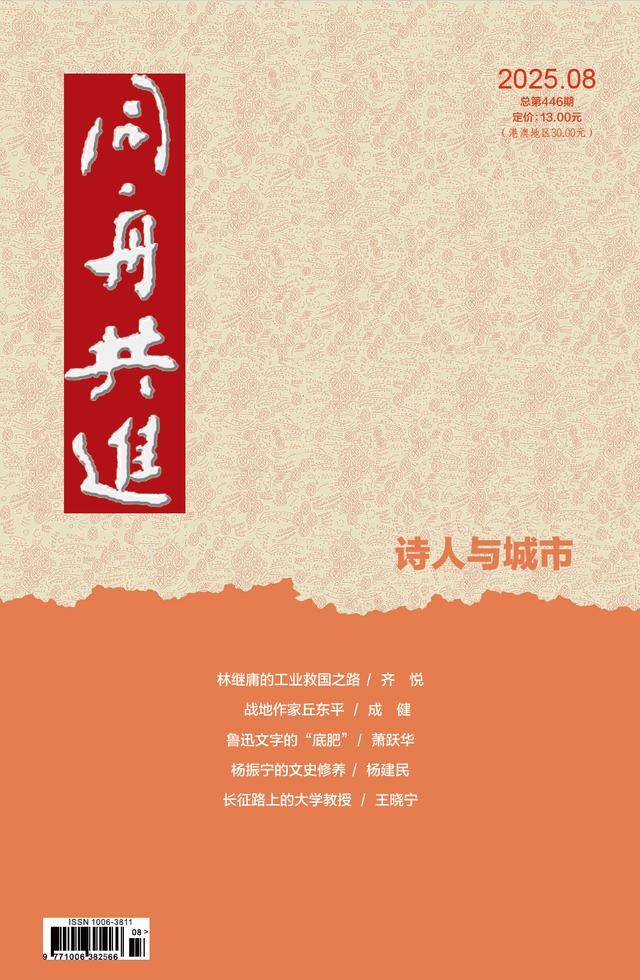
我囫囵吞枣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个版本的《鲁迅全集》,自不量力撰写了《我对修订的七点拙见》(《博览群书》2023年第12期),难入专家法眼,权当抛砖引玉。
读书譬如吃菜,凡人各有所爱。我爱读鲁迅著作,个别篇章不时翻翻,经典名句经常引用,却很少琢磨文字背后的东西,光荣的缺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客观存在。甲辰岁末,从头至尾拜读孙郁大作《鲁迅与国学》(商务印书馆2024年8月版)15篇长文和后记,又旁及其《鲁迅的暗功夫》《鲁迅与国学续话》,深感他20年来执著于这个话题的韧劲。孙郁历任鲁迅博物馆馆员、副研究员、馆长,为完成学术使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天时地利人和,孙郁不负“东家”,可亲可敬可佩。
湘人鲁荡平诗曰:“人如植物书如粪,下得肥多长得深。”我从孙郁笔下依稀看到了鲁迅文字的“底肥”——
其一,国学
孙郁说:“鲁迅自己,是不太喜欢国学这个概念的。对于同代一些学者的所谓国学研究,也偶有微词。但他与旧的遗产,有诸多纠葛,不少见解得之于古人启示。”这是阅历家之言。
鲁迅参加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会稽县试,尽管没有考上秀才,四书五经是下过苦功的,旧学修养与浙东学派渊源甚深。他从官修史志和儒家经典中读出破绽——“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譬如:“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法三章者,话一句耳。”(《小杂感》)又如:曹操“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还有“《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战国时谈士蜂起,不是以危言耸听,就是以美词动听,于是夸大,装腔,撒谎,层出不穷”(《文学上的折扣》);《四库全书》编辑中的“全毁,抽毁,删去”,等等。
鲁迅一面批判陋儒的思想,一面呼唤远古的遗风。他对文化遗产的兴趣主要在经学之外,主张广收杂览,雅俗同读,文野比较,不受专业限制,多读摆“史架子”之外的东西:“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毕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这个与那个》)那些不同于儒家叙说的文字,既有审美的奇色,也包含着不凡的思想。鲁迅广搜秦砖汉瓦、断编残简,抽丝剥茧,溯流穷源,小心求证,取其精华,颠覆了象牙塔的思维模式,看到了纯粹学者所看不到的东西。孙郁《对章太炎学识的取舍》一文分析认为,这是因为鲁迅“认识历史和文化,走两条路,章太炎、胡适仅一条路,差异很大。他从章太炎那里学到以古证今,而自己有时又能以今证古。后者是他特有的本领,其杂文通晓古今的洒脱之状,大约与此有关”。
博采古今,为我所用。鲁迅的书法,金石气扑面而来,这是他在绍兴会馆日复一日钞碑帖的熏染,没有古人的暗示,断不能仿佛一二。他设计北京大学校徽,图形有秦汉瓦当的影子,线条跳动着天地相通的伟意;著述编辑、封面设计常常择取汉代画像,以此呼应远古的灵光,那种痴迷在文字间不经意地暗自流动;《故事新编》描写上古和先秦的人物与环境,从金石考古角度切入历史与艺术世界,展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精神宇宙;杂文古代史料信手拈来,医术、地理、民俗、方言、圣谕、墓志、诗集文录等“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聚焦服务于他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根底是人性的批评这个主题。我们重读《看镜有感》《论睁了眼看》《娜拉走后怎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友邦惊诧论》《拿来主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论雷峰塔的倒掉》……不得不叹服鲁迅的思想穿越时空,许多观点至今仍引人思考。
“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古书与白话》)鲁迅从旧垒中走来,14000多册藏书构筑了他学识博杂、兴趣广泛的知识谱系。他洞知其中的弊端糟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往往制敌于死命。但读鲁迅的文字不太容易发现这些书籍的影子,孙郁《魏晋文脉之考察》《非儒与非孔的理由》《对庄子的另类叙述》《晚年文本的墨学之影》等篇章告诉我们:鲁迅笔下的六朝气、庄子气、杜甫气等全藏在这些文本背后。
其二,西学
鲁迅的西学,发轫于江南陆师学堂下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这所仿照德国体系设立的新式学堂颇多域外气息,鲁迅的德文、日文就是在这里开蒙的。他从这里瞭望世界,陆续接触了赖耶尔《地学浅说》、代那《金石识别》、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加藤弘之《物竞论》、涩江保《波兰衰亡战史》等译著,熟悉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凯撒、华盛顿、卢梭、孟德斯鸠等西哲的名字,发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图景。尤其是桐城派气息的译著,古老与新鲜的文脉有趣嫁接,打开了新青年认识世界的大门。
东渡日本求学,鲁迅的思想逐渐显示出异样的特色,《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等作品,已不再是梁启超式的简单的东西对比,而是现代文明观的呈现。他感慨古印度、古希腊和希伯来的文明进程与艺术“灌溉人心”之美,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那里受到启发,觉得清代读书人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自我,大声疾呼精神界战士。孙郁说:“鲁迅哲学的本质是战斗的。即看透而不逃逸,以自己的热能去温暖冷酷的人间。”鲁迅不同于儒释道的精神突围,填补了传统文化留下的空白。
留学期间,鲁迅开始研究佛学。他藏品中有许多佛学书籍和佛教绘画拓片,抄写过《出三藏记集》《法显传》,珍藏了弘一法师墨宝,辑录的《古小说钩沉》中有许多佛教文学的片段,还自刻《百喻经》送人,精神气质散发出佛教的基因。这就不难理解:普陀山寺庙里有鲁迅语录,内山完造称“鲁迅先生,是深山中苦行的一位佛神”,宗教领袖赵朴初对鲁迅敬佩不已。
在精神最为压抑、困顿的时候,鲁迅喜欢用佛经里的词汇和意象表达自己的心情,并非从信仰层面,也不是消极地引用,而是从艺术的审美方面借力,表述自己茫然无助时的心态及挣脱苦海的坚毅之情。他晚年大力倡导新兴的版画运动,就来自佛教艺术、欧美木刻和日本浮世绘的启示。鲁迅始终关注大众、扶持青年,和形形色色的敌人作战,其境界恰是佛门的一种追求。孙郁认为:“中国读书人那么深地写出底层百姓苦楚的不多,鲁迅的悲悯一直贯穿写作的始终。……我们打量鲁迅深层的世界,可以看到他与释迦牟尼这样的大哲同样非凡的一面。”鲁迅临终前念兹在兹:“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也是生活”……》)他一生写作千变万化,但根底不离慈悲、自尊、施爱这些基本信条,寒冷中的温情成为其文字里永久的景观。
“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致力消除这种民族、文化、个体之间的“不相通”,其《捷克译本序言》说:“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他拓展这条道路,从《域外小说集》开始躬亲文学翻译,着重向国人介绍东欧、北欧文学,尤其是弱小民族作家富于怒吼、反抗精神的作品,其中包括不少文艺理论著作。
鲁迅自嘲:“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他又酷爱俄罗斯文艺,自己动手并帮助他人翻译了不少作品,弥留之际念念不忘《死魂灵》第二部的出版。鲁迅出发点十分明确:“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他深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鲁迅放下创作从事翻译,其译著与著述各占其半,可谓筚路蓝缕,厥功至伟。
其三,生活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之家,鲁迅看清了世人的面目。他留学日本,原本想学医回国后救治像父亲那样被耽误了的病人,战时就去当军医。可当他在课堂上看到正要被日军斩首示众的国人画片,左右围着“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深感凡是愚弱的国民,哪怕体格健全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他归国后辗转杭州、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目睹或亲历了辛亥革命、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军阀混战、读经尊孔、打压学潮、北伐战争、外族入侵……
行万里路,读“无字之书”。鲁迅对历史和社会的深刻洞察,使其文字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震撼力。《阿Q正传》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社会和一群畸形的国人的面貌,塑造了不朽的流浪雇农的典型形象。《狂人日记》呈现出变形人间的变形心理,以礼教为核心的文化环境把人置于非生非死的苦境,无疑是传统变异的罪过。《祝福》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人间,生动地刻画出女主人的悲戚和顺从……
从鲁迅小说中,孙郁察觉现实灰暗与人生真相背后的悲天悯人:“阿Q、闰土、祥林嫂、孔乙己、单四嫂子,都是要被救助的可怜之人,鲁迅以无限慈悲之心照出存在的本真,希望笔下的人物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进入人的世界。”鲁迅杂文针砭时弊,尖锐泼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影响和激励着吴南星(吴晗、邓拓、廖沫沙合用笔名)、马铁丁(陈笑雨、张铁夫、郭小川合用笔名)、唐弢、何满子、曾彦修(严修)、邵燕祥等后起之秀继往开来,给新中国副刊史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笔。
鲁迅重视社会实践,甚是忧心:“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睽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通讯(二)》)他常想给《语丝》投稿,但一句也写不出,连“野草”也没有一茎半叶,不由感叹:“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两条路。”(《厦门通信(二)》)他告诉李小峰:“本地也有人要我做一点批评厦门的文字,然而至今一句也没有做,言语不通,又不知各种底细,从何说起。……如果竟来批评,岂不要笑断真的批评家的肚肠。”(《厦门通信(三)》)
后来在《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应怎样才会好?》里,鲁迅讲了八条:“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郑重向全党推荐了这篇文章,并抽取其中四条作了解读。
集美学校邀请鲁迅演讲,校办秘书打招呼:“校长的意思是以为学生应该专门埋头读书的。”鲁迅不管校方招待如何隆重,校长殷勤劝吃劝喝,回答道:“那么我却以为也应该留心世事,和校长的尊意正相反”。(《海上通信》)鲁迅对如何读好“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见解独特,反对当“书橱”,倡导自己做主、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别让脑子给别人跑马。
他说,读书“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读书杂谈》)鲁迅对多位北大学人陌生起来、微词渐多,孙郁说,这是因为:“刘半农已经没有斗士精神,钱玄同油滑有加,废名过于‘苦雨斋’色彩,……”这些昔日的五四运动健将如今躲在象牙塔里,沉静在自己的园地中,早已失去当年直面现实的勇气,精神的烟火气和时代感弱化了。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孙郁《留给北大的遗产》《对庄子的另类叙述》《批判旧戏的几种理由》等篇章,与读者分享了鲁迅作品的国民性反思、现代性探索和批判精神、文化启蒙。他说:“鲁迅的思考是与社会和人生密切相关的,所以没有匠气与迂腐气。”这正是鲁迅作品比同时代其他作家作品活得更长久的原因。
(作者系北京日报社副社长)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 萧跃华







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