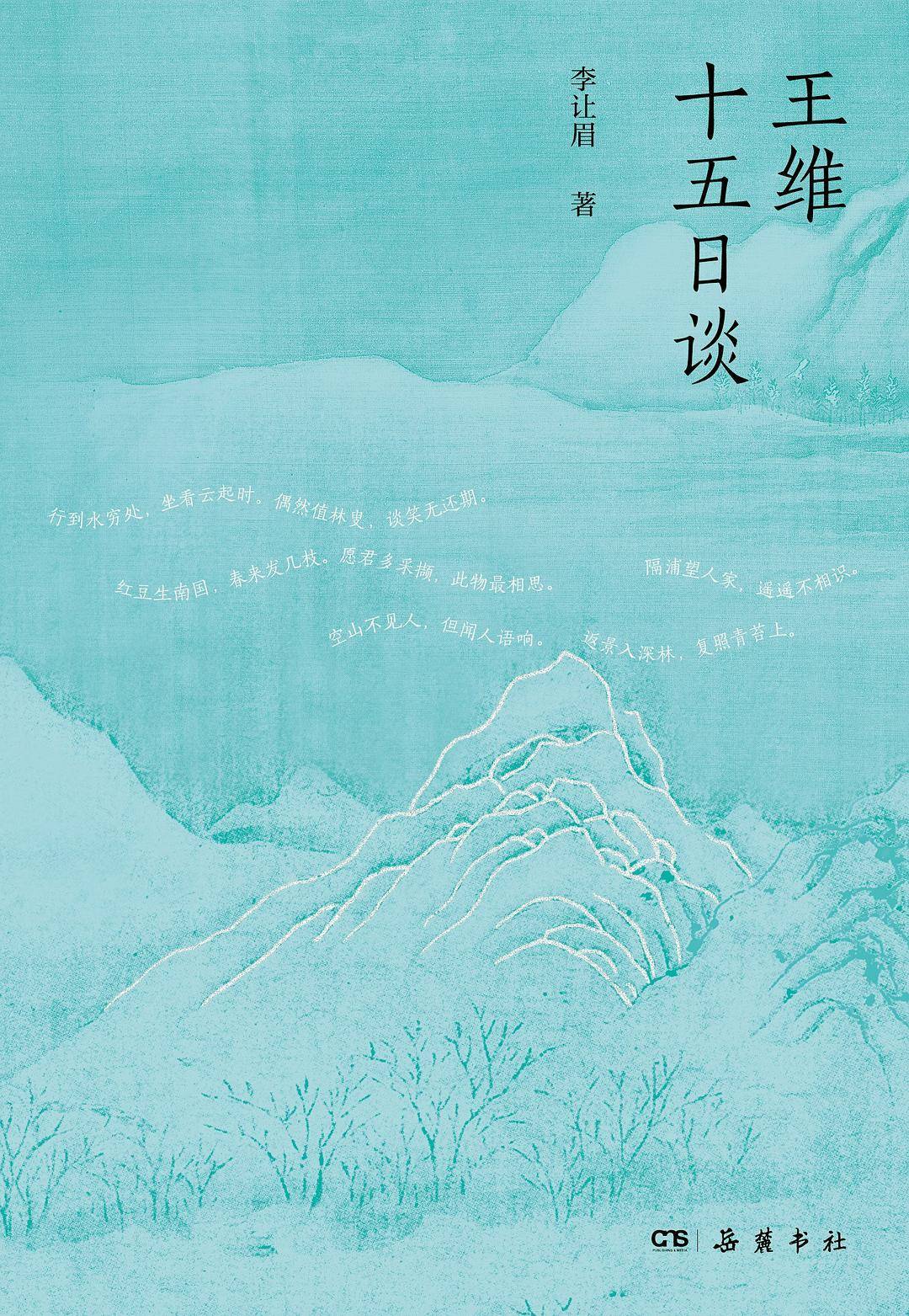
《王维十五日谈》
作者:李让眉
版本:浦睿文化|岳麓书社 2025年9月
相伴十四天,这场漫谈该进入尾声了。乘着色相与音声随王维走过了这样一场长谈,我想在告别前补上几句自己的感受。
不知你翻到这一页时,我们的世界又迭代成了什么样子——但从盛唐回到此时此地,我想或许你会有同感:时间穿过我们的速度与古人的已不再相同。
现代文明对效率的追逐将我们推入了更为迅疾的相对时流:太常寺从《龙池乐》走到初步律化的春祭礼乐用了十四年,而若交给人工智能辅以专家反馈,这种级别的探索最多几个月就能完成;王维从长安去辋川,任是快马加鞭也总得半日工夫,可如今我们驱车出西安城区后走沪陕高速则最多只需一小时车程。今时今日,人确实较农耕时代活得轻易:我们拥有更大的时空自由,能用一辈子的时间经历他们几十辈子也无法想象的变化。这当然可以说是一种幸运,但幸运背后总有代价,多与快,也不是永远意味着好。
我不打算做社会学讨论,只说个体的感觉。当环绕四围的时间太过稠密,我会觉得身心不太畅快,一如座上的清风若变成浓雾,人就很难再有深呼吸的冲动。这不仅是个比喻——被各式屏幕包围,看各种信息飞掠时,我们的呼吸确实会变得既浅且快,与世界的交互也将日益稀薄。
这或者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并没能追随湍急的时流彻底摆脱“从前慢”:风拂上面颊的速度没有变,浪打上沙滩的频率没有变,黄鹂一声啼鸣的长度没有变——树增一圈年轮、花经一回开落,都仍遵循着一种远大于人类野心的自然节律。当我们习惯于手忙脚乱地追逐技术奔跑,就只能日渐与世间万物格格不入。
人们怀念着慢的时代,却已渐渐忘记该如何作为一个生命去毫无机心地与天地同处。“行到水穷处”或还不难,但大多数人都已失去了“坐看云起时”的能力——梦想在山水间终老的人真若丢掉手机去山水间独坐,恐怕多难心境安稳地撑过五分钟。我们已经习惯在日夜川流的信息中飘荡,殊难将自己再交给一泓不波的空潭。
这是我觉得当代更需要王维的原因。跟随他,或者能让自己重新参与进这个可触的世界中去 ——用生命,而非头脑。
王维是一位虔诚而本分的艺术家。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他的表达是与感受相适配的,一入复一出,既不私藏,也不加力,让万物好好地流过他,再经由他的孔窍回归万物。以此,我们可以在他的创作中,看到人与世界正常交互应有的样子。说来似乎很自然,但若你尝试过艺术表达就一定会明白,这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声色在身体律动上的复现
先说入口端。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通过世界,然其间所获一定千差万别。人们常将之简化为观察力的差异:正如同样走过一条山路,有些人天然就能看到更多物种,分辨更多颜色……但这种评量标准与我们要讨论的诗性感受并不完全匹配。在视觉思维本位下,观察力裁定的仍是大脑对信息的占有量,并没有考虑身体的参与度。
事实上,我们可以介入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色声之外,尚有香味触法。能将视听得来的信息整理为身体的感受,才算是真正与事物缔结了联系。
我想引王维《过香积寺》中的“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作为注脚。依诗评家找诗眼的习惯,你当很容易关注到“咽”字与“冷”字的不俗。自明而清,人多盛赞这两个动词用得工巧:“五、六即景衬贴荒凉意,‘咽’字、‘冷’字工”(明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咽’与‘冷’,见用字之妙”(清沈德潜《唐诗别裁》),“泉遇石而咽,松向日而冷,意自互用”(清张谦宜《絸斋诗谈》),“五、六特作生峭,‘咽’‘冷’二字,法极欲尖出”(清卢麰、王溥《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但即使是公推的新警,这两字仍不似杜诗那般有谋一事、制一器的锤炼感,究其原因,大概就因为它们只发乎身体感受,而无关作品意识。
“咽”是喉头的震颤,“冷”是体肤的凛栗。它们都是被动而自然的身体觉知,随势而发,因境而生。耳中的泉声与眼前的松色与作者没有构成物理接触,但在王维诗中,它们类化成了两种直接而明确的体感。
这种身体直觉的获取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轻易。先说“冷”字:对今人而言,冷暖色已是俗成定义,用“冷”来饰写青色也就顺理成章,并不稀奇;但在王维的时代,我国传统画论还未形成色彩心理学的理论自觉(冷暖色的说法要后推至清初恽寿平时代方才初步成型)。要将色彩转化为切实的生命感受,他没有任何概念可供援引,只能依赖认真而诚实的身体觉察。“咽”字亦然,吞咽发乎软腭的承重,听到石隙水声感到喉头上提,完全是一种托身入物的表达。
这种发乎直觉的感官整合也许来源于王维多元的艺术经验。声音与色彩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来自造物者的“无尽藏”,它们客观存在,适人取予,但于他却更复杂些:他明乐理,又工绘事,实际参与过音乐和图像的创建,就更容易用一种创作者的思维去面对它们。
对音乐家来说,声音远不止意味着耳膜接收到的刺激,它更是簧片的颤动、琴轸的旋转、指腹的游移、唇齿的姿态、气息的形状……他们会自然地被声音代入熟悉的韵调,然后自然地激发起自己的演奏经验来。举“松声泛月边”中的“泛”字为例,以“泛”写声,便与古琴指法中“泛音”之“泛”出于同源。琴人奏泛音时左手甫触即离,声质空灵如“孤鹤唳空”,故而蔡邕论琴尝以泛音喻天籁(散音、按音则分别对应地籁与人籁),在此句中与高处松声在月下的声光烁动参想,就极为精准——这样写声,是娴于琴理之人才有的感受。
绘画亦然。我们前面曾说过,每种色彩都有自己独特的质地与性格,它们被一点点提炼、打磨,然后循画师生浓淡、定排布,方成风景。王维写景时笔法便往往兼工带写,暗伏画理,如“白云回望合”之“合”,便很显然有回笔渲淡的姿态在里面,“积雪带馀晖”之“带”、“千里横黛色”之“横”也莫不如此。这种因图景辨笔势的本事,也是画师独有的。
声色在身体律动上的复现,是我希望能通过重读王维诗歌打开的诗境入口。有实际作用于身体的感受加入,物象才不再是一滑而过的即时信息,能经由诗人的生命进入诗的边界。
及此就可以谈到输出了。丰沛的感受力是诗人不可或缺的禀赋,它主张创作冲动,非为王维独擅,但作诗时能有几分感受说几分话,不用诗艺催动个体扩张或情感升华,这份克制却是大诗人中相对少见的——很少有人甘心这样写诗。
大诗人多有恃一字驱策山海的语言能力,如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中的“蒸”“撼”,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中的“坼”“浮”莫不似此——设若我们去掉这几个动词,“泽气云梦,城波岳阳”“吴楚东南,乾坤日夜”亦是不坏的四六骈文语料,但失去或蒸腾或延展的动势神采,诗的领控空间却显见狭窄了许多。
事实上,唐代云梦泽早已填淤成陆,孟浩然当然不曾实地见过水汽上腾,岳阳楼高仅二三十米,杜甫也很难凭栏看尽东南一带的断隔与开张——站在洞庭湖畔,他们真正拥有的只有一片苍凉的湖水和古往今来几个单薄的地名,可经过诗歌一番整理,种种传说与图志就这样在他们手中震荡开来,演化出了百倍宏阔的气象。
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大的自由,占据更广远的时空。我们总会不自禁地被更“大”的东西吸引,是以很少有诗人能抗拒文字表达的扩张欲——那是语言的本能,正要遵循这种本能,诗才好辐射开来,触及更多的灵魂。
意象如此,情感亦然。诗人喜欢用语言驱动感受,让诗在情感的延长线上继续滑行,这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属于文学创作者的愉悦:诗与诗人的主导权在语言领控下即时互换,像乘滑板路冲,我们很难说跃上板后那段滑行就不属于诗人——即使可能已经脱离了他的速度极限。
这通常就是很多情诗被指“情至深则近伪”的缘由。好诗能让我们看到最极致的情感表达,但事实上,人在真正饱满的情绪中很难作诗,再清浅流畅的诗也需要理性参与。不客气地说,所有看似至情至性的诗,都是诗人在情绪回落后,在语言思维的驱使下让自己再度冲向高峰的一种感官拟合,在这个过程中,诗人会受到语言的强烈诱惑,也将不再满足于止步个人的觉察:诗语会带动他们继续向上飞升,甚至乘之腾化,以领受更具快感的情感体验。
但这不是王维的写法。
王维文字能力高绝,值应制或应酬需要亦能造奇象、开广庑,但单纯面对自己时,他是诚实与克制的。同样写山中阒寂,不闻鸟声,柳宗元会横推千里,作“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好为后面的孤舟独钓聚焦出反差之势,而王维则仅止于“谷静唯松响,山深无鸟声”,停在此山此时,不为加持孤独的烈度去肆意展张意象。写感情亦如是,同值丧妻伤心,元稹能将悲痛推至“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高度,以圣人之高、神女之美将自己的感情极度神圣化,王维却只如白描般带了一句自陈,“心悲常欲绝,发乱不能整……颓思茅檐下,弥伤好风景”,不肯以他人事典稍加渲染。
他的诗歌拥有绝大的容量,偏偏表达的尺度控制得又极为精准:不受时序拘束,不作空间架叠,不循人事助推,刚好能容你完好地经由诗歌逆向回归到感受,不增不损地找到独属于艺术家的身体直觉。
若说大多数诗人的诗是酒,王维的诗就更近于药——在他人向往强大与力量时,王维更看重平整和通顺,也可以说,他人求的是精进,而王维找的是回归。
精进往往依赖技术的破发,回归则只会指向欲望的自抑。至此,我们也不妨回到今日开篇的话头,要跟着信息的奔流飞驰,还是依从自然的节律放缓,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不过,在时代急流的冲刷下,王维的诗或许能让我们重拾一点不被裹挟的定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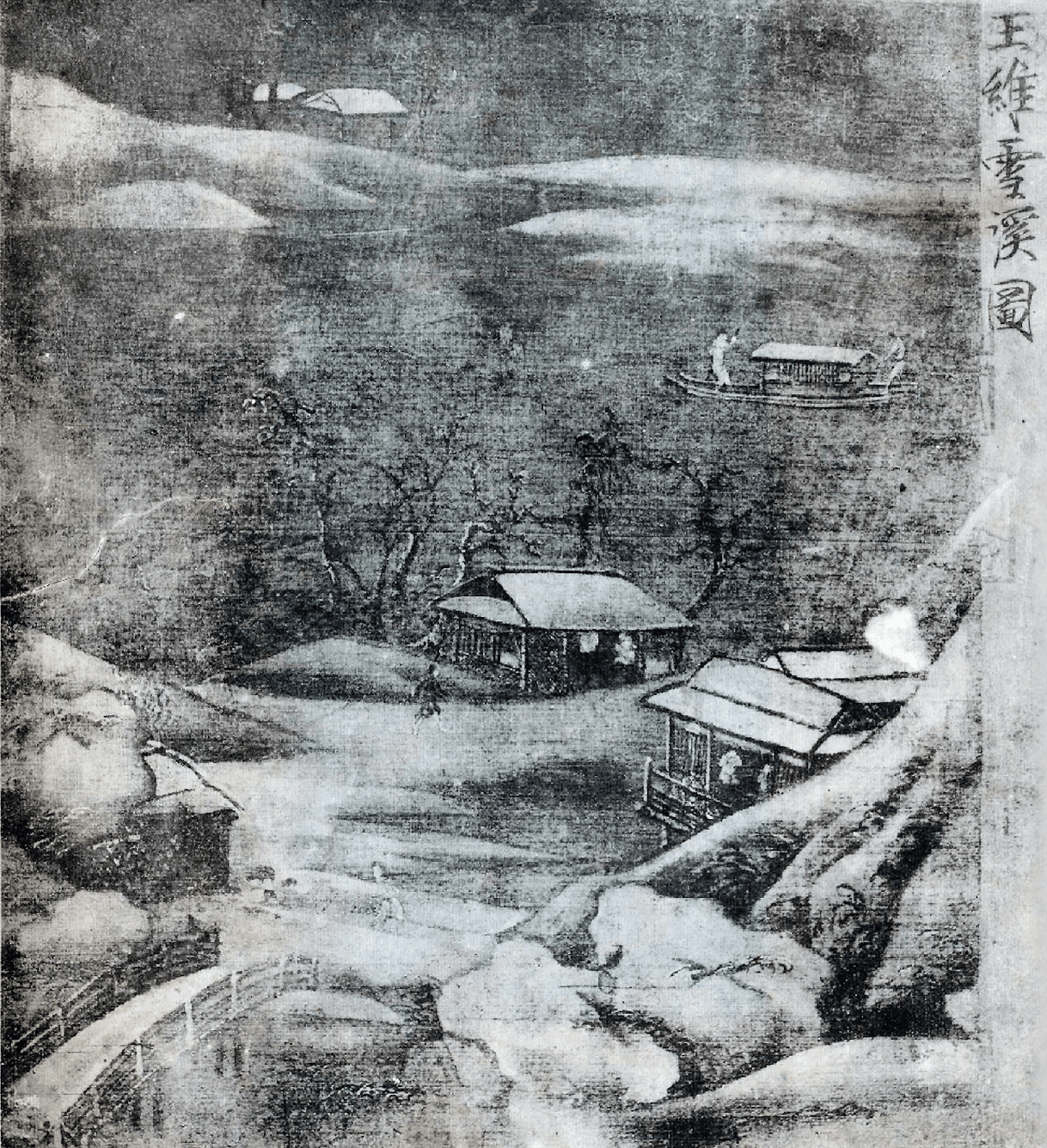
王维《雪溪图》
人与天地最直接的吐纳与交融
说罢读诗,我想再从作诗的视角顺势聊聊我们如今面临的诗学处境。
不知你读到这里时,人工智能的人文创作能力是否又有了突破性的演进,我的闲聊,也只能基于此刻的切片展开:写这本书的这段时间,DeepSeek的出现确实对许多仍在坚持文言诗歌创作的人造成了一些心态上的扰动。
倒不为它写得有多么工稳,人类诗人早已能接受这种程度的冲击——毕竟早在世纪初,我国民间就有擅诗的IT工作者在开发作诗程序了,经过二十年迭代,其成作虽不能说追步唐宋,可写出像模像样的同光体已不是问题,技术特征外显而易于提取的诗歌流派多逃不掉被大规模复制的命运,这在人类世界同样成立。
一种诗风能被凝聚成诗派,往往正因它能给资质普通的诗人一个顺利进入某种成熟表达的机会。在传统的诗歌场域,这种易于复制的确定性可以转变为一种组织方式,将审美志趣相似、创作能力相当的人群快速聚集起来。但当创作权被让渡给机器后,这重社会学意义被消解,其易被替代的弊端也随即显现了出来。
人的聚合本身就是一种意义,但作品的聚合不是。相似的人通过诗歌被拉近后,灵魂会找到更合理的共振方式,与这相比,诗歌结集本身并不重要:一个诗派能生产出两百首抑或两百万首水准以上的诗歌,从任何维度看都无法构成对真诗人的情感冲击。
说回2025年年初这轮DeepSeek迭代。事实上,它令人焦虑的点更多在于机器创作逻辑从稳到新的转向。
农历年除夕前后,一首题为《超新星客栈》的机器创作出现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人们对语言模型极为热烈的讨论。诗的后四句作:“南来星舰贩暗能,北往虫商卖时差。醉客忽掷银河碎:‘此乃故乡最后沙。’”你该能感觉到它还远说不上成熟,纵然引入了大量相对文言语境有些陌生的意象组,但若出于人类诗人之手,大概率掀不起那么大的讨论热度。
自《三体》《银河帝国》等科幻文学走入大众视野以来,很多文言诗人都已颇具野心地开始在物理学框架下对诗歌进行时空拓展了:古代汉语语法弹性高,结构变化也就更多,在传递信息方面也许不及现代汉语准确,但若用于观念建构,却有浪漫而独到的美学价值——只要文言不死,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必然之事。《超新星客栈》引发讨论的点并不只在于它本身,更在于人们突然意识到,一条用以分离作手与庸才的金线似乎要失效了。
我在前面谈起过诗人很难拒绝扩张的冲动,现在我们仍从这个假设出发: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感知力与倾诉欲都会随生命力转衰,诗的入口端也无法避免地一点点收窄。为保持作品的尺寸,诗人会逐步容许语言技艺上位替手,为他撑起诗歌的空间,走向下一步延展。这种延展的底层,其实就是一种交叉的逻辑。
自杜甫通过近体诗逐步探索出网状展开的法门,诗就有了更多样的远方:相较现代汉语,文言更为自由,它不必遵从严正清晰的语法链条,遂能开启更多的拼插端口。
对老杜而言,他的语料与同时代诗人并无太大分别,对交叉的运用主要是依托近体诗的格律黏性把打散的时序、地理与叙事错落编织入自己的情感线。举“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为例:短短一联之间,有巴东,有河源,有人境,有仙家,有真切的伤感,有落空的期待……在平与仄的交错里,它们共同撑起了一个比“因未能追随严武回归长安而伤感的中年诗人”本体要阔大得多的时空想象。
今天,我们面临一个远比唐代丰富绵密的世界,可以用来交叉的要素也就自然更多了:新旧语言可以交叉,学科框架可以交叉,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也可以交叉。一个娴熟于文言范式的诗人若掌握了更多元的信息、能穿梭于更多维度的观念,就自然能引导更复杂的结构,诗歌的尺寸也当然会更大。
DeepSeek创作的那首《超新星客栈》炫人耳目之处就在于新旧语言与文理学科的交叉:它为“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的乐府句式嫁接上了科幻小说中常见的物理名词,又以李白“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的姿态为媒引入《三体》中“宇宙沙粒”的意象。虽然只有意象,还远未涉及具体认识框架,可只这一点点陌生化的接入,就已让一首诗有了被看到的资格。
事实上,这首诗的意外走红映射出的是文言诗歌现阶段的审美方向:人与世界的关系日益浮泛,作为诗内核的生命张力也相应越来越微弱,作为代偿,诗人决定为那个日益衰小的核织出更蓬松的茧,让更多信息可以附着其上,让诗歌更沉重、更复杂,以抵消生命损失的分量 ——走得更极端些,则索性彻底放弃个体视角,让蔓延的结构取代生命燃烧,去完成更可持续的延伸。
这层茧,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交叉”。
这是一条堪称走通了的路。它已形成了丰富的诗学理论与审美标准:织出这样繁复的丝茧不是件容易的事,那需要极广博的见识、极包容的思辨与极敏密的联想,意味着勤奋、天赋与眼界的际会——一定程度上说,在这条路上,信息容量的大小与语言能力的高低,可以最终决定诗人的水准差等。
而DeepSeek这首诗的出现却恰恰让人们意识到,这些如此珍贵而幸运的禀赋突然不再具有被区分的必要:人永远无法占有比AI更广博的信息,对语言的直觉也不可能与基于概率预测的语言模型相比。当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满足于为成熟的诗歌体裁生产合律的标准件,而开始选择笨拙地冒犯诗歌的空间边界,这条区分诗力的金线就注定将被碾碎。
硅基加入创作的新文本时代,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问题——诗歌究竟是空间的诗歌还是诗人的诗歌,换言之,它是一种安放或开拓的方式,还是人本身。
天赋卓绝的诗人总不甘心只做个诗人,他们愿意承担更多的使命,也总想赋予诗更多的意义。自古以来,诗歌的身份一直在这种崇高愿景的推行下演进,也承担起越来越多元的功能。它牵引礼仪,推倡政令,映带历史,构建叙事,阐释哲辨,开垦语体……能做的事似乎越来越多,但到今日我们却意识到,当诗可以脱离诗人作为一种功能存在,人工智能当然也不妨雄心勃勃地站在我们身边,来争一争诗的定义权。
技术依赖理性却不信任灵性。它抗拒本能,也就终将指向普适的标准与个体的坍缩。当所有语言层面的技艺都已能通过概率的推演被迅速习得,我们或许该回过头去,看向层层解剥之后,诗最终不能被算力替代的、属于“我”的部分。
谈应制诗时我们曾探讨过“言”与“意”的关系,也看到了双方消长过程中诗的滋生。如今,当“言”之一道被引入了远较人类强大的竞争者(或谓建设者),我们对“意”的把握也就越发关键:能不能在天地间掂起自己的重量,在人海中看到自己的面目,在概率中确认自己的语言,这对诗来说很重要,对我们亦然。而在重拾个体感受一道,王维是一位绝好的接引者。
我们说过,在王维的认知里,自我的重要性很低——这让他避过了大多数诗人无法避免的自恋。自恋往往伴随着潜意识下的自我美化,与强烈的被注视妄想:那喀索斯在水波中看到的自己,一定兼带着他下意识的美学创作。当诗人内倾太过,作品意识会随之产生,那个真实的、与世界实际发生着关系的自己会反而慢慢模糊——习惯于跟随更具美学侵犯性的语言去感受世界,他们会甘心牺牲掉一些真实,成就一种更完整也更高明的述说。
王维的好处,就在于他的表达中看不到这样的权衡。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语言能力本就足以精准地复现自己的感受,不必犯险弄虚,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没有被作品意识驱动的野心,遂不必扭曲自己的体验,裹挟更宏大的语言去推动诗境的开张。
王维的诗典雅而坦诚,能广博地接纳,又平顺地返还,他精准地复现了一位具有立体多维感知能力的人与天地最为直接的吐纳与交融。我们读太白时少能出神,读老杜时不敢出神,但读王维却是不妨随时出神的——若太专注于揣摩他的诗艺,反如买椟还珠:他的诗不是一只漂亮的盒子,你可以随时从中蜕出、飘散,也可以随时自由归来。

米芾(传)《王维诗意图》
生本寻常
最后,我想借一首我们最熟悉的诗来结束我们这十五天的长谈:《相思》。
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这首诗异文很多,上面引用的版本来自清代王士禛《唐贤三昧集》:它与《唐诗三百首》中我们熟悉的版本最为接近,只是“春来”被换成了“秋来”。其实,自唐宋至清中期,诗中此处都作“秋来”,我们熟悉的“春来”反而是晚近所改。
红豆又叫相思子,生于岭南,该是王维知南选时所见。它“秋间发花,一穗千蕊,累累下垂;其色妍如桃、杏”,能在萧肃的人间开出难见的鲜妍。其果实像细皂角,到次年春日,“荚枯子老”,荚中小豆掉出,“零落可拾数斗”,这就是王维劝朋友采撷的红豆了。萎落的红豆坚固而美丽,“赤如珊瑚”,“鲜红坚实,永久不坏”,比花朵又多了一重恒定的尊严,因形如血泪,故名为相思。当地人爱它形名俱好,常用来赠给朋友与情人,或存置银囊(韩偓“罗囊绣两鸳鸯,玉合雕双鸂鶒。中有兰膏渍红豆,每回拈著长相忆”),或穿成串珠作首饰;亦有人因它颜色鲜亮,用以嵌骰子(温庭筠“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好取个吉祥意头。
这样细说红豆习性,倒不单是为论证“秋来”一说的合理,我想提醒你注意的是,以唐人的图景常识看来,红豆是种非常不合时宜的作物。《相思》起手二句,写的就正是它的特异:红豆生长于远离长安的南国,发蘖又赶在百卉凋零的秋日,时时处处都透着与人间运转秩序的不调和。
对诗人而言,这样的植物最合喻用:既可写贬谪,也可写不遇,既可哀“举世皆浊”,也可赞“坚持雅操”,用笔稍作拧转,就能把种种个体的情势鲜明地架出来。但王维却并没有选择这条路。
这首《相思》中全不见一丝执拗与勉强,一“生”一“发”,和顺如歌板,把一颗特立独行的种子调驯得自然而然:“红豆生南国”是植根,“秋来发几枝”是萌芽,“愿君多采撷”是结子,“此物最相思”是得名,从未生写来眼前,从秋日写到春日,结空成色,顺理成章。离开时空的制约,它同样是应开时开,应尽时尽,开不骄矜,尽不折堕,既不特立于独异,也不焦灼于从众——或许就因他的处理实在太过平淡,才让晚近不熟悉红豆脾性的清人将“秋来”改成了“春来”:他们很难意识到这首诗在写的本是一种多么有性格的植物。
王维看待红豆与任何人间草木都无二致,但正因如此,后面委婉含情的“愿君多采撷”才见珍贵。它不必因自己的不同担负任何期待,却也没有泯没自己的面目和性格:生本寻常,但每一个个体,也都值得人心怀温热,珍重相托。这是王维在走过这样的一生后,最终留给人间的态度。
十五天漫谈及此兴尽。我们也终将穿过彼此的生命,走向更邈远的万物,一如秋来枝发,春及实采。
感谢这期间那些曾隐现于我们身畔的光痕与声影,更要感谢你长久的陪伴。
本文为《王维十五日谈》一书中的《第十五日》一章,大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李让眉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发表评论 评论 (3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