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磨镜 白居易
衰容常晚栉,秋镜偶新磨。一与清光对,方知白发多。
鬓毛从幻化,心地付头陀。任意浑成雪,其如似梦何。
磨镜篇 刘禹锡
流尘翳明镜,岁久看如漆。门前负局人,为我一磨拂。
萍开绿池满,晕尽金波溢。白日照空心,圆光走幽室。
山神妖气沮,野魅真形出。却思未磨时,瓦砾来唐突。
白居易与刘禹锡以 “磨镜” 为题各作一诗,看似同咏一物,实则借 “磨镜” 这一寻常意象,照见了两人历经宦海沉浮后的不同心境 —— 白居易的《新磨镜》是对衰老的坦然接纳与对世事的超脱,刘禹锡的《磨镜篇》则是对蒙尘的抗争与对光明的坚守。两首诗的差异,恰是两人人生阅历与精神底色的生动映射。
一、先识 “镜” 之喻:中唐文人的 “磨镜” 情结
在中唐语境中,“镜” 绝非普通日用品,而是承载着多重寓意的文化符号:它既是照见容貌的工具,也象征着照见本心、辨明是非的 “精神明镜”;而 “磨镜” 的动作,则暗含着 “拂去尘埃、恢复本真” 的期待 —— 这与刘、白二人历经贬谪、渴望洗尽冤屈、重拾初心的人生境遇高度契合。
两人均在 “永贞革新” 后遭遇长期贬谪:刘禹锡被贬近 23 年,从朗州到连州、夔州、和州,辗转南方偏远之地;白居易虽贬谪时间稍短,却也因直言进谏被贬江州、忠州,晚年虽回洛阳任职,却早已看透官场倾轧。“磨镜” 之题,正是他们借物咏怀,将半生坎坷与心境投射于诗中的载体。
二、白居易《新磨镜》:衰容照见豁达,白发里藏 “梦” 与 “超脱”
白居易作此诗时已近晚年(约太和年间,其 60 岁前后),此时他已从 “兼济天下” 的仕途理想转向 “独善其身” 的生活态度,诗中虽有对衰老的感慨,却无悲戚,更多的是一种 “认账” 后的通透。
1. 首联:“衰容常晚栉,秋镜偶新磨”—— 日常里的 “偶然惊醒”
“晚栉”(晚起梳头)是晚年慵懒生活的细节,“衰容” 是早已习惯的状态;“偶新磨” 的 “偶” 字是关键 —— 不是刻意磨镜,而是偶然为之,却恰恰因为这 “偶然”,让后续的 “惊醒” 更显真实。这处细节藏着白居易晚年的心境:他并非刻意回避衰老,只是日常的琐碎已让他对 “衰容” 麻木,而新磨的镜子如同一个 “意外的提醒”,将他从平淡生活中暂时拉出,直面时间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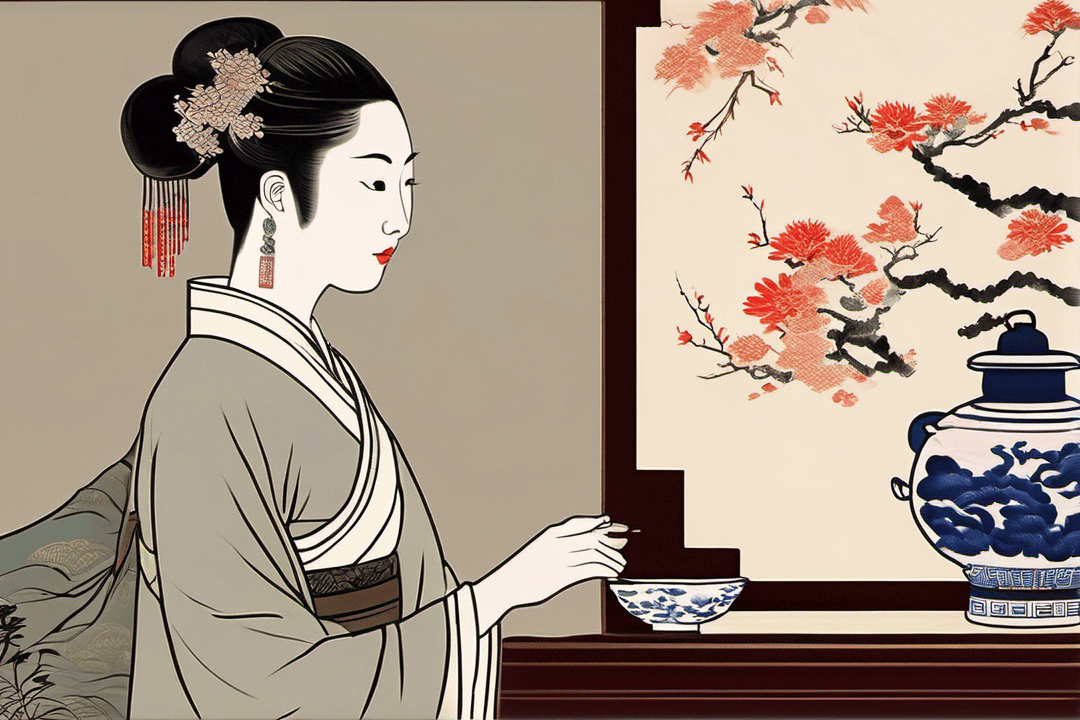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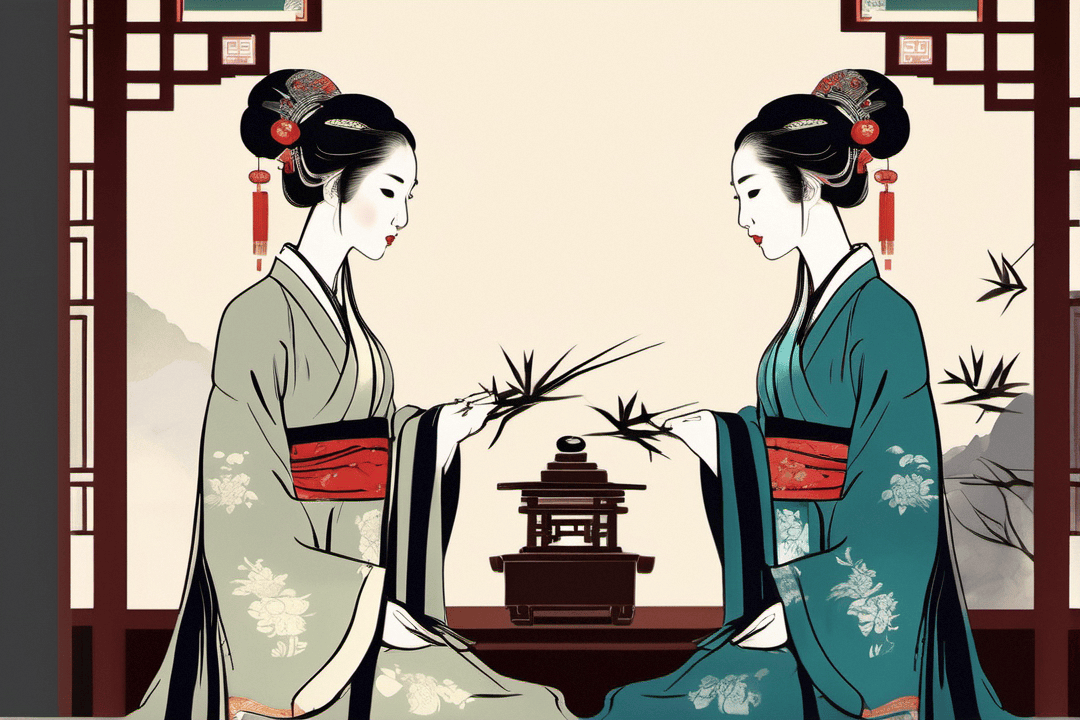
2. 颔联:“一与清光对,方知白发多”—— 直面衰老的 “坦然”
“一与…… 方知……” 的句式,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一种 “哦,原来如此” 的平静。白居易没有像李白 “高堂明镜悲白发” 那样的悲叹,也没有像杜甫 “白头搔更短” 的焦虑,只是客观陈述 “白发多” 的事实。这种 “坦然” 源于他的人生阅历:历经江州司马的失意、忠州刺史的奔波,晚年回洛阳任闲职,他早已明白 “人生七十古来稀”,衰老本是常态。与其悲叹,不如接纳 —— 这正是他晚年 “知足常乐” 生活哲学的体现(如《醉吟先生传》中 “抱琴击磬,饮酒赋诗” 的闲适)。
3. 颈联与尾联:“心地付头陀,其如似梦何”—— 从 “身老” 到 “心超脱”
如果说前两联是 “照见身老”,后两联则是 “照见心明”:
三、刘禹锡《磨镜篇》:尘镜照见抗争,光明里藏 “气” 与 “坚守”
刘禹锡的《磨镜篇》同样作于晚年,但与白居易的 “豁达” 不同,诗中处处透着一股 “不服输” 的劲 —— 这股劲,正是他被贬 23 年却始终未改的 “诗豪” 本色(白居易赞其 “锋森然,少敢当者”)。
1. 首联与颔联:“流尘翳明镜,为我一磨拂”—— 从 “蒙尘” 到 “重明” 的抗争
2. 颈联:“萍开绿池满,晕尽金波溢”—— 光明重现的 “壮阔”
如果说白居易的 “清光” 是温和的,刘禹锡的 “金波” 则是壮阔的:磨镜之后,镜面如 “绿池开萍” 般澄澈,如 “金波溢满” 般耀眼 —— 这组比喻极具画面感,“绿池”“金波” 都是明亮、开阔的意象,与前文 “如漆” 的黑暗形成强烈对比。这不仅是写镜面的变化,更是写他心境的变化:历经磨难后,他的 “本心之镜” 并未被摧毁,反而在 “磨拂” 后更显光明。这种 “越挫越勇” 的精神,与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的豁达不同 —— 后者是对未来的乐观,前者是对当下 “光明重现” 的坚定信念。
3. 尾联:“山神妖气沮,却思未磨时”—— 坚守本真的 “清醒”







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