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苏轼北归前,特意绕道南华寺,站在六祖惠能真身前,竟失声痛哭。
几月之后,他留下八个字,把一生的沉浮写进临终遗言。
那一跪,到底压了多少心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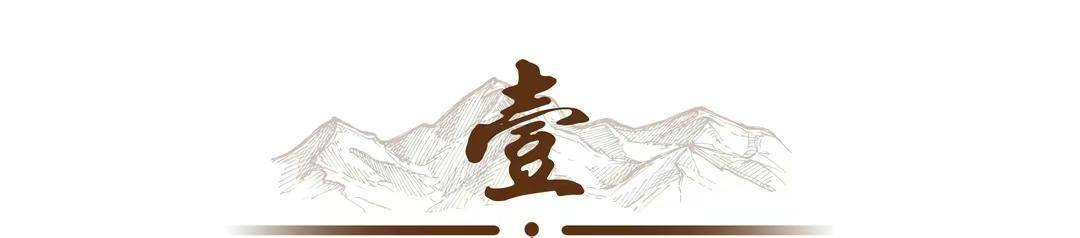
苏轼一辈子,走得不顺,但活得通透。从中进士那天起,他就注定在风口浪尖上过一生。
他21岁考中进士,文章惊艳朝野,连欧阳修看了都摇头赞叹,说这是将来能独步文坛的人物。少年得志,才华横溢,意气风发,但朝堂之上,从来才气不是护身符。
王安石变法动了根基,他偏偏站在了对面。劝不动人,倒惹一身骚。
几年之内,职位起起落落,从京城被贬到杭州、密州,再到黄州、惠州、最后远放海南。
一贬比一贬狠,一路越走越荒,朝廷不给他回头的路。

真正的转折,是1079年那场“乌台诗案”。
诗写得再好,也救不了命。御史参他“讥讽朝政”,朝廷震怒,苏轼锒铛入狱。一夜之间,从翰林学士变成阶下囚。
生死一线之间,他才第一次看清权力的锋利,也看清人生的无常。
他被贬黄州,地位是“检校水利员”,名义上是干活的,其实就是边缘化的安排。但从那以后,他彻底变了。
住在东坡,种地、写字、散步、闲谈,他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定风波》《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些名篇,不是少年意气,是中年顿悟。
“一蓑烟雨任平生”“人生如梦”,不是写出来的,是熬出来的。

苏轼的佛缘,其实早就有了苗头。他祖父苏序笃信佛教,家里经书不少。小时候的苏轼看得懵,但留下了种子。
年轻时在京城,与佛印禅师多有来往,两人你来我往,讲经辩禅,诗文相对。那时候,他更像是拿佛法当文字游戏,看谁讲得高,谁说得妙。
可人一旦跌落谷底,开始追问“为什么是我”。黄州时,他遇到一个叫庞居士的人,两人常谈佛法,最常谈的是“不二法门”。
“无住生心”这句话,彻底打开了他的心结。
什么叫无住?就是不执、不依、不缠。心不系在任何处,才有自由;一旦执念太重,就会被绑住,生出苦来。

从那时起,他的诗不再是单纯地写风花雪月,而是多了“看破”的味道。苏轼开始把佛理带进生活,把顿悟写进诗里。
他说“我本修行人”,不是客气,而是他真的相信,自己的这一生,是在“修行”中走过的。
政治是一种修行,流放是一种修行,甚至诗酒茶烟火,也是一种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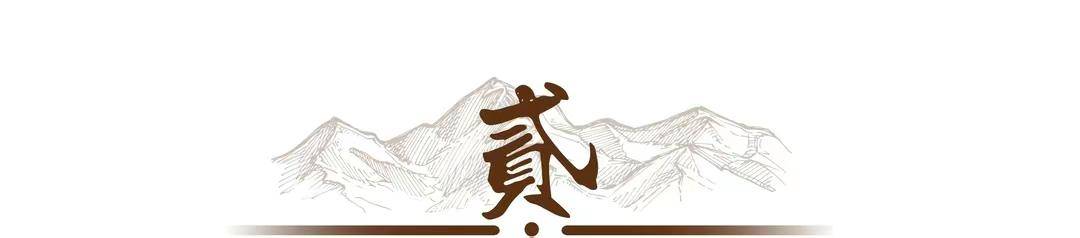
1094年,苏轼又被贬了。这次,是惠州。
从黄州到惠州,比的不是远,是更远。那时候他已经57岁,身体不好,心里却意外地平静。因为他早就不指望再做大官了,只想着走一步,看一步。
他离开江西,路过韶州,那是六祖惠能圆寂之地,南华寺就在城郊。
六祖的真身供奉在寺中,是禅宗南宗的大本营,佛门极重的一处地方。

苏轼动了心。走到这里,不进去一趟,是心里过不去的。
他提前三天开始斋戒,吃素、洗浴、净身,然后换上常服,不带随从,独自入寺。
进入大殿,他一眼看见六祖真身。
端坐不动,眉目安详,闭目而笑,像活着一样。那一刻,他站着不动,像是突然被定住了。
他没有说话,跪下长拜,然后起身,走到后堂,在纸上写下一首诗:
八句诗写得坦白,也写得通透。
他认了这一生的不顺,不怪人、不怨天,只说自己有“一念失”。是贪?是痴?是执?他没说。
但那句“我本修行人”,分量太重。他不是来参观的,是来朝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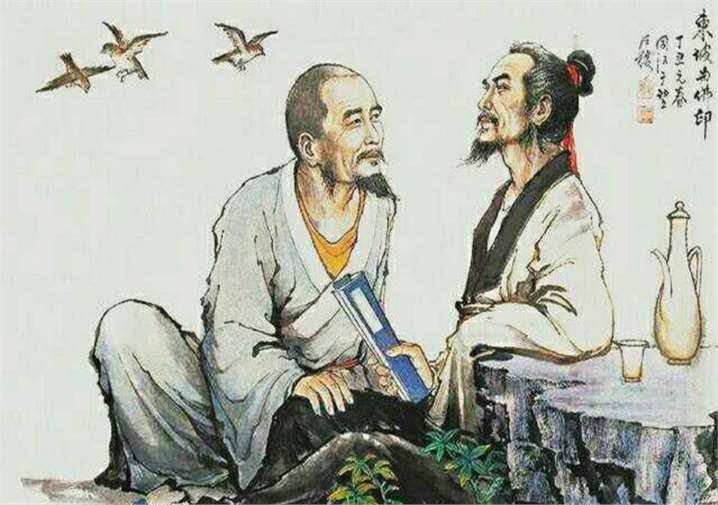
住持重辩接见了他。两人谈了一夜,一边讲禅理,一边谈命运。苏轼说到后来,只留下六个字:“云何见祖师?”
这不是疑问,是心声。他知道六祖没说话,但那尊真身的存在,已经在他心里回答了自己。
他明白了:不在朝堂,不在流放,不在高楼,不在诗文,真正的祖师,在心里。

他告别南华寺,走向更远的贬地——惠州。那一次的见祖,也成了他后半生修行的转折点。
从此以后,诗里佛意更浓,说话更轻,说笑更淡。
他开始真正信佛,不是信佛像,而是信这“放下”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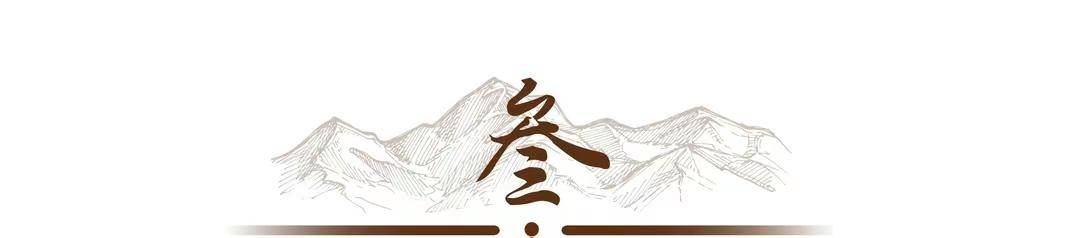
元符三年,苏轼遇赦北归。此时已63岁,身体每况愈下,走一段路就要停歇。
按最短路线,他应直走粤北入湖南,但他偏偏绕道,回了南华寺。
那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南华寺。
一行人到韶州时,他主动要求停下。住持已换,寺中迎他的是明禅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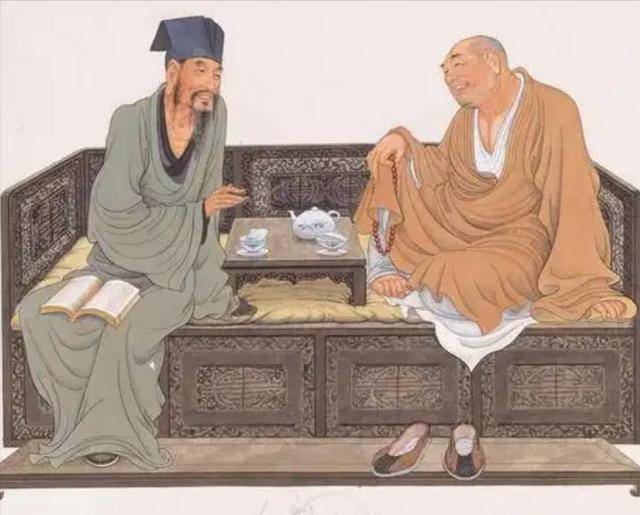
苏轼不进客房,直奔祖堂。他站在六祖真身前,不语,不拜,眼眶泛红。
片刻之后,他蹲下身子,像孩子一样哭了。
明禅师在《南华长老题名记》中记载此事:“泪雨霰,洗绮语砚,以祈六祖慈悲”。
苏轼带去的文具、纸墨全被泪水洒湿,连笔都写不下。整个人站在那像失了魂。
他没写诗,只留一句八字话:“吾生不恶,死必不坠。”
这八个字,后人读来各有解释。有人说是生无愧事,死无惧报;有人说是看透人生,认命但不屈。
但他自己知道,这是他对六祖讲的最干净的一句话。
一生起伏,百种遭际,走到这一步,他只留下一个交代——我尽力了。
离开南华寺后,他一路北上,到常州时已经病重。消息传开,老友、弟子陆续赶来。床榻前,他不言官、不讲诗,只谈一件事:随缘。
临终前,他嘱咐苏迈等人:“勿哭,任其自然。”维琳长老来见他,只劝一句:“莫忘西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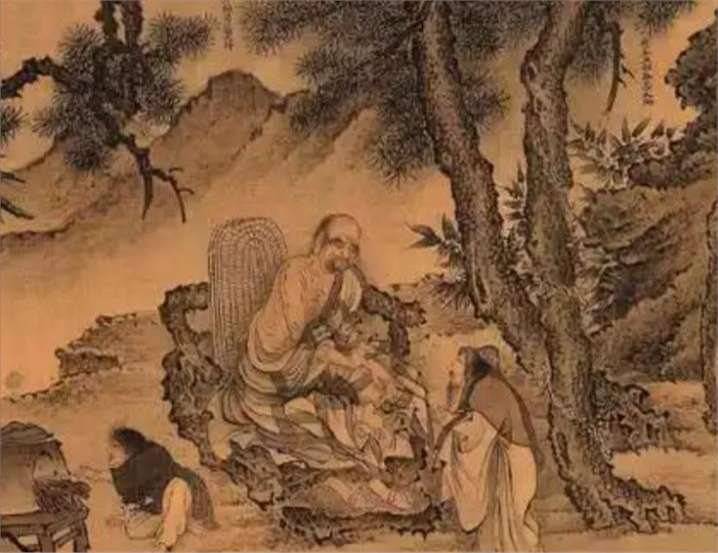
苏轼闭眼前只说:“去留由天,非我能求。”语气平平,却把所有抗争与执念交还于空。
这位写下“大江东去”的文豪,最后安安静静地躺在常州西门外。
没有钟磬,没有送殡的队伍。只有一张床、一口气、一颗终于归于平静的心。

很多人说,苏轼最通透的岁月不在北宋朝堂,而在海南岛。
儋州是当时的化外之地,路难行、水难喝、人难教。但苏轼到那后,没怨一句。亲手搭学堂,自己种菜、教书、写字、抄经,过得像个老农。
他收下不少学生,最出名的是黎子云。两人论禅谈道,无拘无束,写《海南岛记》说:“此心安处是吾乡。”这不是自欺,是实悟。

他不再反抗命运,也不再追问结果,而是从佛学里找到一种现实的“安顿”。
他写《观潮》,说“庐山烟雨浙江潮,到得还来别无事”。眼前巨浪滔天,他却淡淡一笔。这不是不见苦,而是见过了,才学会“不惊”。
临终后,他的遗言广为流传。那八个字,“吾生不恶,死必不坠”,被不少禅门看作顿悟之语。
清代《南华禅寺志》收录了他的《锡泉铭》《苏程庵铭》,很多文人僧人都称他为“居士典范”。
现代佛教研究者认为,苏轼晚年思想已非纯粹的儒者或文士,而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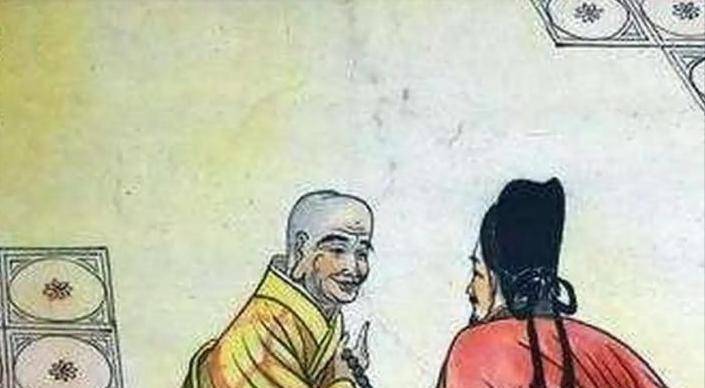
他不入寺为僧,不出家为道,却能在文字中融通三教,留下完整的一种人生态度。
岭南一带,至今不少书院讲学中还会引用他的诗、记他的事。
他早就不是单纯的诗人、词人、政治人物,是一种心境,一种在苦中悟、在失中放的人生态度的代言人。







发表评论 评论 (4 个评论)